Equitable exit strategy is required: lessons learnt from Hong Kong’s current resurgence of local outbreaks among individuals from highly deprived neighbourhoods.
A Warm Welcome to Prof. Nancy S. JEC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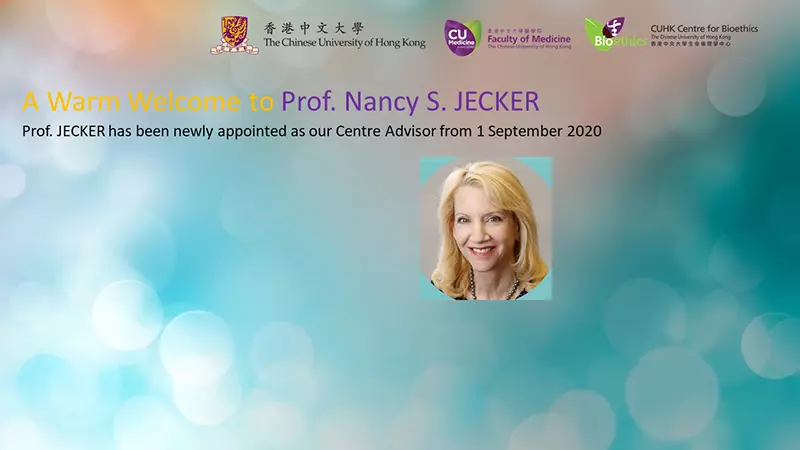
We sincerely welcome Prof. Nancy S. JECKER to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Prof. JECKER, Professor of Bioethics & Humanities of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 Medical School in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ppointed as our Centre Advisor from 1 September 2020. She holds Adjunct Professorships at UW School of Law, Department of Global Health and Department […]
Heartfelt gratitute to Professor Alastair Campbell for his guidance and contributions to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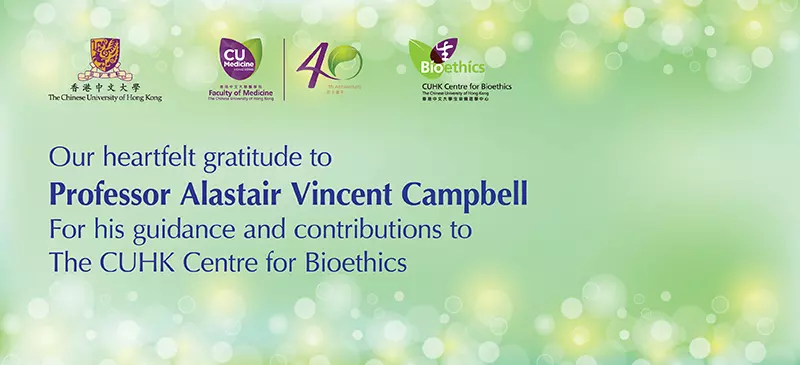
Professor Alastair Campbell was served as Senior Centre Advisor for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from September 2015 to August 2020. Thank you Professor Campbell for his guidance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Centre over the past years! (Click on the flipbook below to view the thank you messages to Professor Campbell)
A Warm Welcome to Prof. Nancy S. JECKER

We sincerely welcome Prof. Nancy S. JECKER to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Prof. JECKER, Professor of Bioethics & Humanities of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 Medical School in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ppointed as our Centre Advisor from 1 September 2020. She holds Adjunct Professorships at UW School of Law, Department of Global Health and Department […]
Heartfelt gratitute to Professor Alastair Campbell for his guidance and contributions to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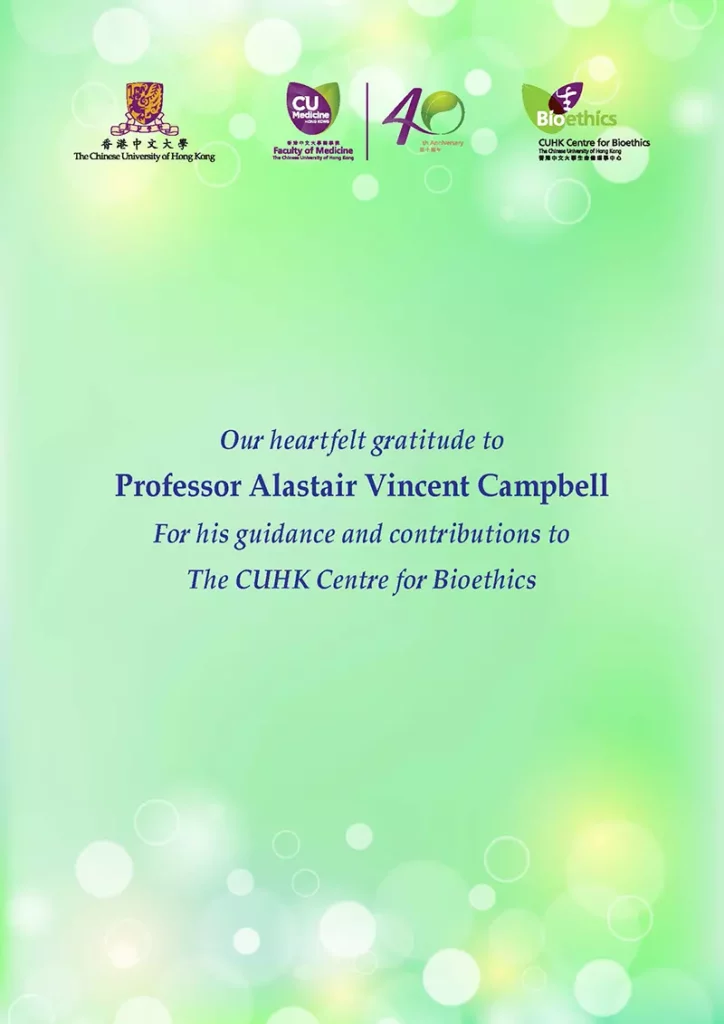
Professor Alastair Campbell was served as Senior Centre Advisor for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from September 2015 to August 2020. Thank you Professor Campbell for his guidance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Centre over the past years! (Click on the flipbook below to view the thank you messages to Professor Campbell) link: https://apps.med.cuhk.edu.hk/bioethicsflipbook/mobile/index.html
染疫長者的治療取捨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31.8.2020)

全球新冠狀病毒病案例已超過二千三百萬,死亡人數逾80萬。各國的個案死亡率(case-fatality rate)差別很大,從1%到15%不等。 這取決於一些本地因素,特別是患者中高齡和體弱長者的比例、COVID-19核酸檢測是否廣泛應用於輕度癥狀病例的篩查和診斷,以及醫療系統的應對能力有無超限等。 在香港,我們最初數月的個案死亡率非常低,遠低於1%,但在「第三波」疫情死亡數字迅速增加,因為病毒已侵入年老人口群體尤其是護老院舍。視乎未來的護老院舍疫情,香港的死亡率可能會接近2%。 死亡率上升固然與染病人群的高齡有密切關係,但也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近期的死亡數字。 8月5日《明報》有一段新聞特寫,題為「坪石八旬夫婦先後病殁 有長者絕望 最後一程拒插喉」,有受訪的醫院前線醫護人員提及,在某些情況下,有些長者在病情迅速惡化時堅決拒絕「插喉」(intubation) 和呼吸機支援,即使很可能死於新型冠狀病毒病,他們也不情願接受心肺復甦和深切治療。同一版也特寫了一對痊癒出院的英國老夫婦,他們在去澳大利亞途中過境時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在屯門醫院經歷數周深切治療後,挨過了危險時期,非常感激醫護團隊和香港的醫療服務。兩段特寫放在一起並排閱讀,反差很大。是不是有些老年的染疫病者真的在「絕望」中放棄了治療的機會? 「自決」還是「絕望」? 我在臉書上談到,以「絕望」為標題,用詞可以斟酌,因為如果長者是經過醫護人員解釋(以及勸說) 之後,決定不願接受呼吸機和深切治療,那麼他們可能是自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 ,不一定是因為絕望放棄。在醫學倫理,病人能自己作主(即使意味著放棄一些有益有效的治療)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而尊重病人意願是一項重要的倫理原則。這段短評引發了一些回應,多數朋友同意我的看法 (得到一些Like), 其中有醫療專業人員也有業外人,大家看來有點共識。然而,有朋友留言提出疑問: COVID-ID並不是無法治療的絕症,假設一個長者接受深切治療的話,能有20%的生存機會,他卻放棄不低的生存下去的機會,那是合情合理的嗎? 在倫理案例分析,這是典型的原則性衝突:尊重病人自主原則(respect for autonomy)、行善裨益原則(beneficence) 是可以產生矛盾的。 分析並不太複雜,大約是這樣:醫護人員在專業上有義務首先考慮治療對病人的益處,以及評估治療的風險或傷害(副作用或併發症)。評估治療的利弊會形成專業對治療方案的意見,但專業建議是受到病人意願的限制。無論在普通法或醫學倫理,在精神上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士,治療必需得到患者同意,病人對是否接受治療有最終的決定權,無論該治療是否被醫生視為有益。 當然,我的朋友也很清楚這些原則和基本分析——他本身就是一名盡責的執業醫生。我意會他的問題其實來自一個不同的關注點。病人同意或拒絕的決定必須是基於充分的資訊,才是「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這些資訊有時不是完全冷靜接收的,無論是在急症或久病狀態,病人可以有多種情緒反應:恐慌、否認現實、抑鬱等等;在某些情況下,認知判斷能力甚至會因病徵而受損,例如肺炎造成缺氧可能會影響精神狀態。在一般精神狀態下病人能決定自己的治療,但忽然被問及是否插喉時,他當場的反應未必是理性的。在法律上,病人自主醫療決定是毋須證明自己的決定屬於「理性」,但從醫德角度可能仍不忍讓他放棄救治。 具體情況細節重要 這點疑問正好說明了,良好的醫療實踐需要的不僅僅是黑白分明的倫理分析和道德立場。在實際情況下,個案的具體細節是極其重要的,倫理分析不能取代良好和細心的臨床溝通。 「具體細節」是什麼意思?例如那對英國夫婦基本健康,互相關懷而享受人生。在病房他們分開但有時間通過手機互相討論,最後接受包括呼吸機的治療,醫生憑經驗解釋,需要大約兩個星期判斷肺狀況是否好轉;在另一個同樣年紀的病人,情況可能大不相同,或者他患有多種頑疾,靠輪椅行動和住在老人院。 在我的朋友提出疑問的情景,他假設長者尚能活動行走,平日也可以出外用膳,即是比較接近那雙生活狀況較佳的英國夫婦,而不是院舍內的嚴重殘疾老人。但是這樣對比時也要特別小心:我們可不要輕易判斷什麼樣的生命更值得生活下去。說不定坐輪椅的長者在護老院裡仍然珍惜自己的生命,還不準備很快去世;另一方面,活動自如的老人也可以基於自己的人生觀,當重病來時,不希望忍受侵入性治療以換取一點生存機會。最終要還是要由他自己作出判斷取捨。 好的臨床團隊會知道如何平衡病人意願和醫療意見,常規醫療程序也必須容許與病人和家人作合適的溝通。以上的討論還只涉及能夠自己做決定的老年病人。在急症病房實際情況,可能多達三分之一高齡病人有認知障礙。當他們沒有能力做出決定,醫生就要與家人根據病人的最佳利益制定具體治療方案。
Association of living density with anxiety and stress: A cross-sectional population study in Hong Kong.
Centre Director Interviewed by Ming Pao

未來城市:病毒測試與收集DNA的距離 Retrieved from NEWS.MINGPAO.COM (9 August 2020) DisclaimerAll views 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various interviews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only,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r opinions of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為醫學倫理讀《論語》(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3.8.2020)

現代醫學立足於科學,由西醫主導,現代醫學倫理原則立足於西方的道德哲學,兩者都具普世性,但中醫在華人社會依然有其位置,在中國大陸更有政策維護。那麼,在醫學倫理領域,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思想,是否也可以得到有份量的現代地位?這並非異想天開。在我現今工作的生命倫理學範圍,一直有學者認真探索和提倡建設中國生命倫理學。 我年輕時對哲學有興趣,入門是從儒家哲學開始,大學二年級去德國做暑期工,帶了一本《論語》上路細讀,思考當時還有點熱度的中西文化異同問題。近日得空暇,從頭略讀了一遍《論語》,有些想法可以分享。 有學者嘗試把儒家思想注入醫學倫理,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期望儒家哲學能成為別樹一幟的道德理論,從而在現代醫學倫理學得一席位;另一面是期望現代醫學從尊重多元文化出發,也能照顧到中國人病者與家庭的儒家社會特性。在現代醫學教育本來就有尊重多元文化的主張,即使強調科學為本的循證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也強調醫生須把醫學證據與病人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相結合,例如關注少數族裔、新移民和土著族群,尊重多元文化是良好的醫學實踐。 推動儒家思想注入醫學倫理,要面對這個問題:現今中國人的文化和價值觀能否歸結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否還好好存在於中國人的家庭?一般來說,中國人重視家庭倫理,但在西方社會裡,猶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等族裔也很重視家庭,這不能算是很根本的中國特色。 或者在具體的醫患關係中,更嚴肅的問題是,當傳統倫理與病人的個人自主權利發生衝突,怎樣解決? 醫乃仁術 以儒家思想為本建設中國生命倫理學(或醫學倫理) ,一個途徑是從哲學高點出發。孔子學說的核心思想是「仁」,而「醫乃仁術」是歷代對醫道的共識。「仁」的倫理推己及人,從「親其親」出發,仁心仁術即是視病人如親人子女。學者王珏在2009年《中外醫學哲學》發表的論文 〈醫乃仁術:儒家視野下的醫患關係〉,頗為深入地論辯了兩點:其一是,「醫乃仁術」並不等同在醫患關係實行「家長主義」(paternalism) 。雖然仁心仁術是行善原則(beneficence) ,但並非叫醫生不顧當事人的意願,強行代病人作醫療決定;其二是,西方倫理學傳統強調個人獨立自主,預設病人自決是最高原則,這可能含有盲點,因為忽略了人的本質有脆弱性,尤其在生病、受傷,或其他無能為力的狀態中,單單以契約關係理解病人的個人權利,可能還不如醫生視病人如親人可取。文章的結語是,從西方倫理視野的盲點出發,「醫乃仁術」的論述「不僅具有獨立的道德意義,而且很可能成為西方生命倫理觀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對話夥伴。」 另外也有人認為,把paternalistic譯為「家長式」本來就是不必要的貶詞,認為paternalism可以譯作「慈父主義」。上述文章也含有這樣的意思:儒家理想是「親其親」,病人不是陌生人。理論上或者如此,但在醫療現場中,中國式「家長主義」始終是一個問題。要注意的是,在傳統中華文化中,「養不教,父之過」,父子關係並不是「慈愛」的親子關係;而且在現代醫療,醫生與病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知識的不對稱性(asymmetry of knowledge);兩者結合時,在現實中是否真的可以尊重病人權利?這不能輕輕帶過。 還有一點疑問來自現代醫學的「科技主義」。醫學科技日新月異,醫生的醫療建議很容易會被嶄新的科技牽著走,在醫患關係中,醫生若是如父親那樣對待病人,會不會就像一些父母為子女好,塞他或她進名校、催谷成長安排一切,一廂情願地把「最好的」東西硬塞給孩子? 仁心不易辨 在科技主導之下,仁心有時難辨。前年內地爆出賀建奎濫用CRISPR-cas9技術基因編輯嬰兒的醜聞,在國際批評下,他被國家嚴肅處理,成為階下囚。但在此之前,賀建奎曾經作出十分「慈父式」的自辯:HIV病人在內地是弱勢和受歧視的群體,不育的父母也不准使用體外受孕技術輔助生育,賀建奎認為自己的編輯嬰兒試驗不單可讓這些父母能得到有血統骨肉,更能令孩子得到抗愛滋的基因。這是利用中國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思想,加上對基因新科技的知識不對稱,只要「我為你好」,就可以剝削脆弱的HIV病人群體。賀建奎並不是醫生,但在科技主導的醫療世界,也有類似的「仁心難辨」的風險。如果醫生有類似的對新科技的迷戀,而病人視醫生如父,很多問題會出現。 近日重讀《論語》時,我想到,雖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落在醫療現場,「仁」的思想對現代醫學倫理的貢獻其實很有限。醫生對病人要有關愛之心和同理心,這在現代哲學和宗教(例如基督教)已經有很好的資源,例如仁慈(kindness) 和關愛(care) 就比「仁」淺白易明。「仁」很深刻,但一般醫生並沒有需要深究「仁」的本義。我開始覺得,《論語》中那些次一層的德性可能更適合與現代醫學倫理具體對話,正如醫學倫理學的「四大原則」也是一種「中層原則」(middle-level principles) 。例如孔子講「忠信」「誠」「敬」「好學」,具體而深刻,平平常常一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篇第十三》) ,強調恭敬處事出於內心,待人接物不帶優越感,是不簡單的倫理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