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oeconomic gradient in health and the covid-19 outbreak.
抗疫犧牲誰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6.4.2020)

全球疫情在最嚴峻階段,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慘烈,公報的死亡人數早已超過瘟疫的震央中國。早在 3 月上旬,有報道說,意大利一些醫院不得不作出困難決定,深切治療病床不能再收年老的確診病人,麻醉學專科發指引協助前線醫生取捨。那時其他國家地區還在旁觀,直至它們也被疫潮正面衝擊才知道凶險。當時美國的疫情才剛剛開始緊張起來,紐約州剛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我們中心收到來自美國東岸一份報章的電郵,問嚴峻的疫情有沒有影響了中國大陸和香港放棄急救病人的醫療準則。 她特別針對問 Do-Not-Resuscitate order (簡稱 DNR,香港稱為 Do-Not-Attempt- CPR ,簡稱 DNACPR) ,即是有關「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指示。更具體地問,當醫院面對極大壓力,抗疫有沒有影響了對進行心肺復甦術與否的日常醫療決定?中國大陸對 DNR 有標準規範嗎? 遇有媒體查詢,通常我即時會決定是否接受問 — 有些主題並不屬於生命倫理課題,另一些題目則可能超出了我們的專長範圍。 這一道查詢似乎在灰色地帶。它涉及多面向和層次。記者的提問其實是指向緊絀的醫療資源分配問題,但「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考慮本來正是不宜從醫療資源角度出發,因為放棄搶救與否,首先應尊重病者意願(例如病人訂立了預設醫療指示) 和考慮病人的最佳利益(例如延長死亡過程可能並不符合末期病患的最佳利益) 。正常情況,不會先考慮資源問題。 醫療資源樽頸 抗疫時期醫療服務極度緊張,令資源分配難題迫在眉睫。且不說深切治療一張病床難求,即使是前線醫護人員的保護裝備也令人關注著,尤其是 N95 口罩和保護衣。如果供應源源而來,資源分配當然不是一個問題;當疫症全球大流行,各國爭相搶 購,就難以確保供應及時。現在意大利、西班牙的前線醫護人員連外科口罩和手套也缺,德國和美國也告急。有些國家地區還有人在囤積這些緊張物資,之前也有人在誇耀自己一早從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大手搶購貨源,如今意大利、西班牙兩國各有 5 千名以上的醫護人員確診感染,最終可能上百名會死亡。從全球大局看,不理他國死活最終只會做成骨牌式失控。中國大陸的疫情已退,是否應大力輸送物資作外援,抑或優先作戰略性的儲備以防第二波來襲? 保護裝備物資的分配問題對病人並不那麼切身。從病人角度看,抗疫資源緊張, 最大的分配問題是:誰能得到服務?誰的醫療需要被擱置、被犧牲? 執筆時(3 月 28 日),香港抗疫的綜合防線已陷入苦戰,如果新增確診數字高企在每天 50 以上,醫院始終無法負荷。一旦每天新增病例數字迫近 100,樽頸可能出在三處:深切治療病床爆滿、人工呼吸機用盡、負氣壓病房全滿。 醫療緊絀的分配問題不能等用盡資源才來面對。例如深切治療病床,數目從來也是緊絀的,深切治療專科有一套既定的評估方法,按病情嚴重性、對病情能否挽回的預測和配套的需要(例如配合重大手術) ,決定是否接收病人。如果多過一個病人符合接收準則,一般是先到先得,即是說,不會因後面來的一個嚴重病人而「趕走」現有病人,即使後者病情相對較輕。在這種分配機制底下,不會簡單地以年齡作為硬性的分界線。 單憑醫學知識設計的分配方程式不能解決所有病例和情況的問題。在個別灰色或複雜情況,醫生要憑經驗作出判斷。倫理考慮必須合乎情理。 看不見的犧牲 按常規指引作分配是「看得見」的,倫理學的術語是 explicit rationing (可譯作「顯性分配」) ;相反,「看不見」的是 implicit rationing (「隱性分配」) 。雖然現代社會喜歡事事透明,但醫療服務並非工廠生產線,不能也不宜全部指引化,而且「顯性」不一定合理,例如一刀切硬性規定 75 歲以上一律不得使用深切治療病床,無疑完全「顯性」,但很有爭議。 當疫潮急如海嘯,會出現幾個甚至幾十個危急病人爭一、兩張剩餘病床的情況。也不單是深切治療病床,急症病床也會缺的。這時無論製訂指引還是憑醫生判斷,都會極為困難。為避免「見死不能救」的極端狀況出現,一般做法是預先甚至即時削減非緊急及半緊急服務。這多是由各專科部門界定(當然也有些客觀原則,例如非緊急手術) ,屬於「隱性分配」。 […]
Centre Director Interviewed by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

題目︰新型肺炎疫情 Retrieved from YOUTUBE.COM (1 April 2020)
Commentary dated 25 March 2020 on Sridhar Venkatapuram, “COVID-19 and the Global Ethics Freefal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live-in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 randomly sampled survey in Hong Kong.
Data collection for migrant live-in domestic workers: A three-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瘟疫帶來倫理難題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9.3.2020)

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最終命名為COVID-19)疫症始於2019年12月,踏入2020年在全國大爆發後波及全球。香港早於1月4日啟動嚴重應變級別,1月8日已把「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列入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名單,起點並不遲緩,但之後的應對有些猶豫,到2月中旬才站穩陣腳。背景因素當然有影響:經歴七個月反修例突之後,社會積累許多創傷,有些負面情緒甚至可以說夾著痛恨。面對民情牴觸,政府較難從洶湧批評中擷取有用的抗疫意見。 大規模的瘟疫從來都會衝擊醫療系統,釀成社會矛盾,這其實是公共衛生倫理的常設課題,並不是因為「被政治化」才出現挑戰,政治張力只是把挑戰放大了。 例子之一是2月初公立醫院員工的罷工行動,數千名人員參與,佔了醫院管理局前線員工一成以上。這次行動不是按章工作式的抗爭,而是基本上離開崗位,這在香港醫療史上是首次,若是疫症發生在一年前,相信罷工不可能出現。醫護人員罷工自然有人反對,包醫學界的領袖,然而民意似乎多過一半人支持行動,因為行動的訴求是要特區政府全面關閉關口(「封關」),要阻截新型冠狀病毒輸入本港。訴求有相當的說服力,那是來自香港2003年的沙士記憶:當年公立醫院苦戰瀕於崩潰,全港8名醫護及健康服務人 員殉職,其中6位是公立醫院員工。新型冠狀病毒來勢猛,若不及早關閉關口,是有可能沖潰公立醫院防線。 專業職責 面對危險疫潮,醫護人員離開崗位有很多方式,辭職、罷工、拒絕編配到危險崗位都是,在外國還有醫護遷居避疫的選擇。醫護人員對病人有特別責任,並非普通服務行業,因此道德判斷的直覺是,違反治病救人的積極義務(positive duty) 是絕不應當的。比喻的例子包括消防員,消防員難道可以輕言拒絕救火?更強烈的醫學倫理價值觀會認為,醫護救人是「天職」,絕不容許離開崗位損害病人利益。 這個題目在國際上已經討論得很多和很深,主要還是2003年SARS一役引發的。當年加拿大多倫多亦見災情,近三分一SARS病例是醫護人員,有員工拒絕被指派的崗位而被辭職。這些「逃兵」行為沒有得到太多同情,但疫後檢討的結論,並不支持把醫護「天職」絕對化。捨己為人、不離不棄是高尚情操,醫護人員亦不應輕言放棄職責,但選擇這職業帶來的積極義務並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即使是消防員,工作原則亦不會是任何情況底下也要衝入火場。 對這個課題的討論,後來因伊波拉瘟疫而深化。SARS的病案死亡率是百分之十至十三,伊波拉的死亡率在非洲較差的醫療條件下可達八成,醫護的保護裝備往往簡陋,因此是否可以要求所有醫護人員也準備犧牲,是非常困難的決定,不是站在安全位置高唱醫護「天職」就可以合理解決的。 在香港今次事件,筆者並不贊成粗糙地視罷工的人員視為「逃兵」,或政治定性為「要脅」,但經過思考,也不能贊成在這情況底下採取罷工行動。原因是病人所受的影響是實質而直接,對缺了人手繼續工作的同事也增加實質負荷和風險,相比之下,爭取關閉關口(「封關」) 的訴求有迫切但並未清晰界定。每天出入內地的人流大部分是香港人,這也削弱「全面封關」的可行性。當然,筆者的立場也未能好好回應罷工的醫護人員的悲憤質問:「所有人叫政府關閉關口政府也是不理,除了罷工還有什麼可以給政府任何壓力?」這是因為倫理思考能影響現實政治走向的力量是很有限。 分配難題 關於抗疫的公共衛生倫理還有兩個熱門課題:一是為控制疫情而限制人身自由的限度,二是當抗疫暴露醫療資源不足,如何分配才算合理?這兒只略談抗疫時期醫療服務的分配難題。 世界衛生組織出版了一本抗疫培訓手冊,中譯本在2018 年出版(周祖木、謝淑雲譯,《疾病流行、突發事件和災害中的倫理學》,人民衛生出版社) ,其中有這案例:流感大流行持續6 周,醫療系統超負荷,每家醫院的病床都已住滿,每一個呼吸機都在使用,所有衛生保健人員在加班,終於要決定要遲已安排的手術,騰出人手和病床。推遲的手術包括腫瘤病人的手術。全國醫院要各自作出決定,修改急救治療準則。醫院A決定根據通常的「先到先得」次序提供救治,醫院B則決定按病情劃分,只為預期存活時間 6 個月以上的病人提供治療。外科醫生Dr. Smith反對醫院 B 的準則,他有一個卵巢癌病人腸梗阻,如果不做手術將在 2 周內死亡,但病人的預期存活時間也不符合6 個月以上的規定。這是一位有三個子女的 36 歲母親。Dr. Smith要考慮是否違反醫院的規定而進行手術。 這是典型的道德兩難,並沒有容易的標準正確答案,重要的是我們要見到,這是一個真實問題,值得仔細權衡考慮。在香港,每當我們面對流行病疫潮,包括每年的冬季流感高峰潮,我們制度化的反應是不須細想地削減非緊急醫療服務,騰出資源以處理迫切的疫情。這無可厚非,但超越某一點時,真的有其他病人受損,利益被犧牲。以「大局」作為迫切理由,就可以犧牲眼前一些病人的醫療需要?細想一下,豈不是與醫護人員今次罷工的邏輯有些相似?
Centre Director Interviewed by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

議事論事 Retrieved from FACEBOOK.COM (5 March 2020)
Centre Director Interviewed by Ming P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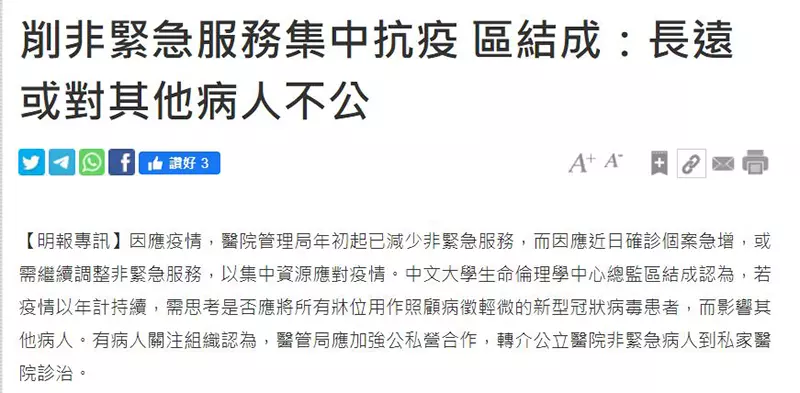
削非緊急服務集中抗疫 區結成:長遠或對其他病人不公 Retrieved from NEWS.MINGPAO.COM (31 March 2020) DisclaimerAll views 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various interviews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only,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r opinions of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Centre Director Interviewed by L’Apostrophe (an international news magazin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Quebec in Montreal) to comment on the case of human germline genome editing by He Jiangku in 2018 and the prospect of CRISPR-Cas9 applications in this feature article “Artificial Evolution – Between Hope and Fear”

Centre Director Commented on The Case of Human Germline Genome Editing by He Jiangku in 2018 and the Prospect of CRISPR-Cas9 Applications in this Feature Article “Artificial Evolution – Between Hope and Fear” Retrieved from L’APOSTROPHE.COM (24 February 2020) DisclaimerAll views 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various interviews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only, and d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