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verty affects access to regular source of primary care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醫護專業與病人私隱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5.7.2019)

醫護專業與病人私隱 六月充滿動蕩和衝突,在緊張複雜的警民與醫療互動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醫護人員有專業責任為病人保密,保護病人的福利,但是否同時需要與警方合作,甚至在某些情況底下違反為病人保密的原則? 這個問題並不是香港獨有的,也不是一個新問題。本文取材自英國兩篇相關文章,並因應香港的情況加以剪裁和說明。 尊重病人私隱,為病者保密,這是專業責任,比普通機構保護個人資料的最低法律要求更嚴肅,因為醫患關係不止是一般的服務合約關係,更有嚴肅的病人對醫護專業的信託。保密是維護醫生與病人之間信任的核心,如果病人對醫生能為他保密沒有信心,就會隱瞞病情,醫治就失去基礎。自古以來,醫生以希波克拉底誓言為醫德,近代《日內瓦宣言》進行了更新,無論新舊,都把保護病人私隱看得很重。醫務委員會和醫學會的倫理守則亦貫徹《日內瓦宣言》原則。 為病者保密的義務不是絕對的,但任何違反保密期望的決定為都必須視為例外,披露資料要遵循正確的原則。 在徵得病者同意的情況下披露資料當然沒有違反保密要求,前提是病人的同意必須是自願的,而且充分知情,包括知道披露資料的後果。有些情況下,獲取病人同意並不可能,例如在深切治療病房昏迷的病人,醫生可能要從病人利益出發,與家人商討病情作醫治決定,這是默許同意的推定。 依法律要求披露 其次是依法律要求而向他方提供資訊。這通常是警方。這是一個可能會令人困惑的範圍。臨床工作上醫護人員必須注意,警方並沒有要求披露病人資料的自動權力,也沒有要求提供醫療紀錄的自動權利。如屬必須,警方需要取得法院命令。但是,在警方進行調查時,醫護人員不得向警方故意提供不正確或誤導性的資料。 舉例而言,如果病者在交通事故發生被送進深切治療部,而一名警官要求醫護人員抽取血液樣本進行酒精測試以助法醫調查,醫護首先要知道這是否法例要求,因為樣本必須是合法的,否則法院不能使用其化驗結果。這些程序應該由書面提出請求,並經確認其為合理。 較少爭議的例子是防止恐怖主義,英國2006年《恐怖主義法》要求專業人員向警方通報任何可能有助於防止恐怖主義行為的資訊,或協助逮捕或起訴恐怖分子。這與當前香港的情景無關,沒有人認為在示威衝突中受傷(即使是橡膠子彈所傷) ,就等如恐怖分子。 如果在醫療過程當中,病人承認犯了嚴重罪行,醫護人員要不要主動報警?這是有些灰色的地帶,因為何謂嚴重罪行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名單。英國的醫務委員會(GMC) 在其指引中未有對嚴重犯罪作出定義,但引用了國民保健系統(NHS) 的《保密業務守則》中給出的例子,包括謀殺、過失殺人、強姦、綁架和虐待兒童致造成重大傷害。 披露必須慎重 GMC 提醒,醫生必須平衡披露對病者的影響,以及不披露的話可能對公眾造成的危害。涉及槍支或持刀犯罪的罪行,與例如違例泊車的罪行當然是不同的。如果病人透露在計劃犯罪,而這罪行有具體的對象,在美國,醫生有義務去警告可識別的受害者,即使這有違病人保密的原則。在英國,醫生可能需要更多的證據去確定其他人有沒有面臨受傷害的風險。總的說來,只要醫生行為合理,沒有漠視對其他人的風險,並且平衡了對病人的責任和社會的責任,他不太可能因為披露與否的決定而被控告疏忽。 最後一個重要的公共利益範圍是公共衛生,特別在疫症流行的情況。香港和英國一樣,有公共衛生(疾病控制)法例,要求醫生被通過強制呈報特定傳染病或與工業有關的疾病來提供流行病學資訊。2003年SARS是香港的集體記憶,當時醫管局、衛生署必須依靠警方協助追蹤病人與接觸者,進行隔離。那是一個醫護人員與警方互相合作的戰役,與今天雙方處於互相提防甚至對立局面,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境脈絡。社會躁動竟然令一些前線人員沉不住氣。在此時節,更有必要回到穩固的專業倫理原則,慎重應對。 在香港近日的情境,考慮到以上的原則,或者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判斷: 警方有權逮捕被合理懷疑干犯嚴重罪行的人,警方也有權在醫院進行逮捕,但是否適宜在動蕩和大規模衝突的局勢中立即去醫院進行逮捕?這並不是一個原則性的道德或法律問題,而是涉及更複雜的、是否明智(prudent) 的判斷; 醫生和護士並沒有義務協助警方去尋找或識別示威抗議中受傷來求醫的人士,更不應協助作出逮捕,除非有法院命令; 如果有醫院行政人員或前線專業人員主動向警方作通報,讓警方拘捕在示威中受傷的人士,這一定是違反專業的,除非是有明確的資訊,判斷若不通報,這些人士對公眾會有嚴重而具體的危害。 參考: K Blightman, SE Griffiths. Patient confidentiality: when can a breach be justified?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Anaesthesia Critical Care & Pain, Volume 14, Issue 2, April 2014. C Wills. Confidentiality: When can […]
Journal Club: “Being Accountable for Medical Errors: Observations on Hong Kong vs Australia”

Date: 11 July 2019 (Thursday) Time: 5:00 – 6:30 p.m. Venue: Room 239, Sino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Dr Alastair Mah, Senior Manager, Patient Safety & Risk Management, Hospital Authority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Powerpoint Slides by Dr. Alastair MAH – “Being Accountable for Medical Errors: Observations on Hong […]
Centre Director Interviewed by Ming Pao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滿城是傷 專訪區結成醫生 轉載自MINGPAO.COM (2019年6月30日) Disclaimer All views 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various interviews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only,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r opinions of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文化差異對(生命)倫理學有多重要?(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7.6.2019)

文化差異對(生命)倫理學有多重要? 四月時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了一場亞太區生命倫理教育研討會議,我們生命倫理學中心的副總監、中大哲學系教授李翰林在會議演講一個有意思的題目,聽者有共鳴。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似乎會對各種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問題便是一例。如果兩個文化在一個問題上互相分歧,兩個意見可以都是對的嗎?如果認為可以,那麼回答這問題的人就是來自「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本文的第二作者區結成在新近出版的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恰巧也觸及這問題,就請李教授簡述一下,以下是演講要旨。 道德相對主義理論認為,道德上的對錯只能參照特定社會群體的信念系統來評價,因此,當社會群體涵蓋一個文化時,道德的對錯便取決於該文化內部的信念。這意味着,意見相左的兩個文化可以都是對的。例如,對於當代東亞人來說,孝順是相當重要的價值,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孝順便沒那麼重要,而這兩個不同的觀點都可以是對的。 然而,道德相對主義是錯誤的。假如道德相對主義是正確的,我們便會完全喪失評判其他文化中人們的言行的資格。不過這將是很荒謬的,因為這將意味我們因此無法批評其他文化中的罪惡。 批評罪惡 數說文化中的罪惡,除了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奴隸制之外,最極端確鑿的例子應是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猶太人施加的暴行。在那一時期,幾乎所有德國人都參與或者至少默許了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行動。我們當然應該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這樣的惡行。 於是有人會問,如果道德相對主義是錯誤的,那麼我們當如何調和以下的兩個事實?其一是,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確存在不少良性的、可接受的道德差異;其二是,有些文化中的行為(比如種族滅絕),即使那個社會的人自己普遍認可,其他社會的人會完全無法接受。有些文化差異並不造成嚴重牴觸,另一些差異卻像勢不兩立,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文化差異對於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有什麼意義? 為解決這一問題,有必要區分「道德」這個名詞的兩種不同含義,即:實證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所謂「實證道德」,是指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事實上所接受和共享的道德。因此,推崇孝道屬於東亞人的實證道德,而允許屠殺或者任意處置(他們所認為的)「劣等民族」則是納粹德國的實證道德的一部分。 「道德」這個詞的另外一個意思是「批判道德」。它指的是用來批判真實存在的社會建制(包括實證道德)的普遍的道德原則、理由和論證。研究生命倫理學的學者通常都是在「批判道德」這個層面來思辨立論。這些學者認為,倫理學具有客觀性,因此他們會努力尋找客觀上正確的道德觀點,不管那有多大的困難。 至於在實證的倫理學(以及實證的生命倫理學)範圍,研究者關心的只是調查群體中人事實上擁有的道德信念和態度,而調查者對之不予批判。如果在一個社群中,绝大多數人都反對同性成年人之間相互同意的性行為,那麼根據(那個社群的)實證道德,同性戀就是錯的。同樣地,根據納粹德國的實證道德,殺害猶太人是被許可的。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純粹的實證道德,或者實證道德本身,並沒有任何辯解(justificatory)的效力。 辯解效力 當倫理學家在論證某種做法(在批判的意義上)不可以被允許的時候,他們會提供理由來說明為什麼這樣的做法是錯的。同樣地,當我們說種族清洗是極端的罪惡的時候,我們會提出道德理由、原則和論證來證明事實確實如此,縱使那個共同體(比如納粹德國的共同體)中的大多數人都堅持自己的行為是可以接受。這表明,如果停留在實證道德層面,無論怎樣盡力仔細地調查研究,所得的實證結果也是無從轉化成任何(批判)理由,來讓我們決定接受或者拒絕那些行為。 根據批判的倫理學的觀念,為一個特定的立場作辯解而提出的道德理由,理應可以在客觀上判定為成立或者不成立。當然,道德理由之為客觀的方式,是不同於科學之為客觀的方式,正如數學的客觀性也不同於科學的客觀性或者道德的客觀性(參見T. M. Scanlon, Being Realistic about Reas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apter 2)。簡言之,某個道德觀點是否合理,必須通過其前提和結論的合理性,以及它所引致的後果來判定。 本文第二作者在《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書中有一節談及中國文化,可以與上述論點互相對照(第99-100節)。在那一節我說,中國文化的確有珍貴可取的思想,例如在《論語.雍也》篇,孔子對弟子談仁政,說博施濟眾還不能算是「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立志之外,推己及人,助他人通達正道,才是「仁」。這可以成為具普世性的倫理價值。中國傳統文化面對現代和世界,如何保持活潑的開放性是很大的挑戰。「去蕪存菁」已是濫調,更不宜借傳統之名,很方便地告訴世界說,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僵固的傳統思想不一定是良好的價值觀。
Workshop on “Ethics and Regul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Date: 12 June 2019 (Wednesday) Time: 9:30 a.m. – 4:45 p.m. Venue: Lecture Theatre 5, 3/F, Cheng Yu Tung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Programme Rundown/Poster: Please click here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List of Abstracts and Speakers’ Biographies: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Powerpoint Slides by Prof. Ainsley Newson – “Tempering Hype: […]
專業倫理的擴充(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0.5.2019)

專業倫理的擴充 在上周舉行的醫院管理局周年大會有一個環節以專業倫理為主題。 我應邀講一個與專業倫理有關的自選題目。我選擇分享最近常在思考的一個範圍:醫學專業是否來到一個時代,需要我們較為寬廣地檢視它的傳統關注範圍,以至反思傳統的專業視野。這些思考,半是緣於觀察近年醫學界如何在一些新聞事件和公共議題上常常處於自辯的位置,不但看來侷促被動,有些意氣反應更顯得defensive。我的看法是十分初步的,其中含有生命倫理學的角度。 在來到現在的中文大學崗位之前,我也有應邀在兩間大學的碩士課程作客座教學。這是一些提供給醫療專業人員的碩士課程,範圍是作醫學倫理和醫療倫理。在開講時我常會借機會展示一張PowerPoint幻燈片,淺談一下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 與生命倫理學(bioethics)之間的異同。 專業倫理主要關注具體的醫患關係,它的背景是行醫與醫務(medical practice)。 專業倫理使用專業行為守則(professional code of conduct),以此規範在醫務中的恰當行為、標準和操守。 這些行為守則並非全與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有關, 有些旨在規範醫生應當如何對待他的專業同行,以至及如何管理行醫的業務方面 (例如醫療廣告、告示牌) 等。 在醫患關係上,專業 規範的焦點是保障病人私隱、知情同意、尊重病人自主, 避免利益衝突,以及維持專業標準(standard of care)。 這當中有一些題目是與生命倫理學共通的, 例如尊重病人的自主權。此外也有其他共同的倫理原則,包括照顧病人的利益、 避免造成傷害,以及公平對待病者。 不斷變化的倫理 傳統上,專業道德是建立在一套穩定的標準和守則的基礎上面。 傳統上專業道德主要是以既定的價值觀為基礎,明確地界定自己關注的邊界或範圍,並且依靠專業的機構和委員會來體現這些價值觀。相對而言,生命倫理學卻是一個恆常在不斷變化和詰問的領域。它歡迎新的關注, 對新的問題進行研究討論。倫理原則是可以爭辯的,事實上也屢受挑戰。 在它的發展歷史, 生命倫理學總是避免受單一學科或個別專業所支配。遇有複雜課題,它往往會考慮到廣泛的倫理和社會影響。在辯論中,法律和社會科學的觀點會被吸納,對持分者的界定也往往從寬, 因此參與者是擴闊到臨床醫生和病人之外。 在現今社會,專業行為守則的條文有時會在法院受到挑戰,無論在本地或外國都有例子。 規管倫理行為的機構加入非專業成員是趨勢,不僅在醫務委員會, 臨床倫理委員會和研究倫理委員會早已是如此。 因為專業倫理重視穩固的傳統,當受到挑戰時,幾乎無例外地,專業的回應總是盡可能保持穩定和不變。在醫學專業內,改革的聲音總是落在下風 。因此,在公眾看來, 專業的改變好像總是勉強而行的, 有時甚至像是不情願改進。 在歷史上,隨著時間的推移, 專業倫理也會發生變化, 儘管可能變化緩慢。 醫學專業尊崇的希波克拉底的古老誓詞(Hippocratic Oath) 來到今天,只有一半內容仍與現代相干,而其中只有幾條倫理原則仍然有效。 現代社會不斷變化,專業堅守的條文便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挑戰。 筆者認同專業道德不可以朝令夕改追求時髦,但有關專業倫理的討論不能封閉。醫學界承受住壓力不肯隨風搖擺,本是值得欽佩的也是重要的,因為有所堅持的專業倫理也是穩定公民社會的石柱。 然而, 對某些課題上,自限於既有的框框和視野難免讓人懷疑。在醫管局周年大會的發言中我列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 擴充專業的視野 其一是,體現在行為守則中的專業倫理有沒有忽略了,在日趨緊張複雜的醫療制度中,醫患關係正在發生重要的變化?專業標準能否孤立於醫療工作的環境,來判斷醫療失誤的責任? 當然, 在紀律行動,處分的輕重有時會考慮到失當行為的背景因素,從而緩減處分, 但事實上,專業紀律的審查不會預先擴大範圍去研究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專業標準能否經常切實執行。 放眼世界,醫療服務質素及安全已成為專門的學問領域,醫療失誤有系統性因素也有人為因素, 如何剖析兩者關係的知識正在不斷積累。不去理會這些知識,一味堅持界定醫療失誤為個人操守問題,是否能公平地反映現實和恰當地問責? […]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Programme 2019/20 [Upda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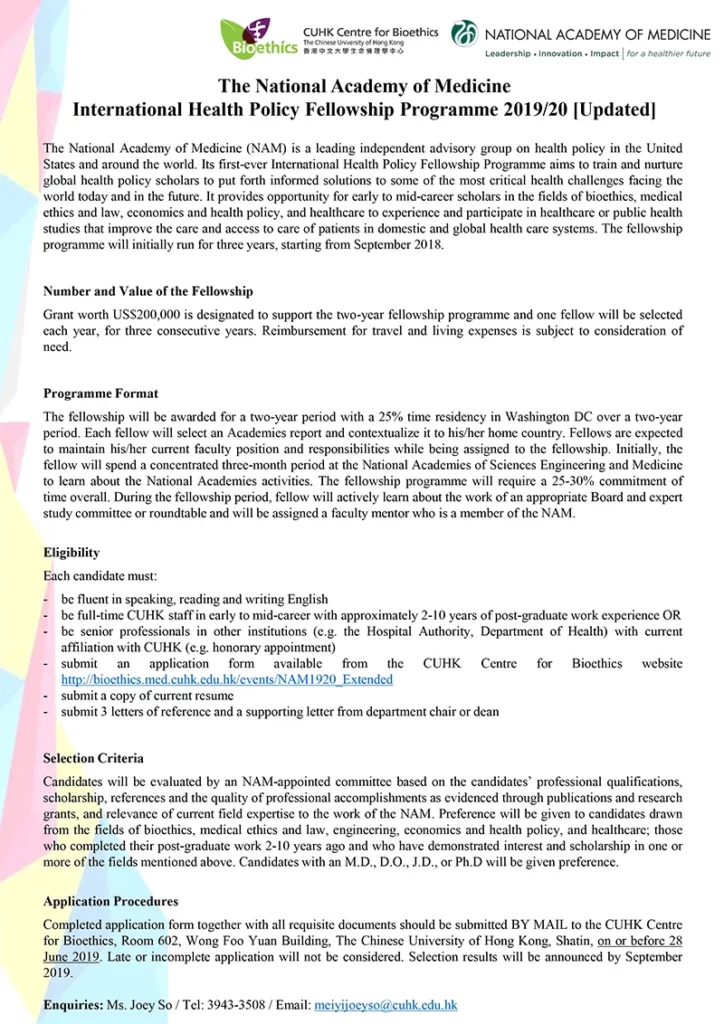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is pleased to call for applications for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Programme 2019/20 with the extended deadline.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NAM) is a leading independent advisory group on healt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Its first-ever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Programme […]
個人須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嗎?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5.4.2019)

個人須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嗎? 高齡78歲的著名哈佛大學哲學家Thomas M. Scanlon今年1月18日來中文大學生命倫理中心的年度Lanson Lecture主講,我們請來香港大學陳祖為教授作評論回應,效果十分好。Scanlon有名著《我們彼此負有什麼義務》(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以縝密思維分析「負責」(being responsible) 的多個層次。在歡迎晚餐上我在他鄰座,談到自己對哲學有基本的好奇和興趣,但未能窺探分析哲學的堂奧。他語帶關切地問:「為什麼呢?」好像在說,有這樣好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去看看呢?這次Lanson Lecture,他講一課「健康的責任與選擇的價值」(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and the Value of Choice ) ,我就認真地聽了,看能否一窺堂奧。 分析哲學的主旨不是為灌輸道德價值。Scanlon有一句名言,是昔年一次精英滿席的聚會上,聚會主人要求每人只准用一句話描述自己的工作時,他信口而出:” There are distinctions to be made, and it is worth making them well.” 這可以意譯為:「事理必須分明,值得致力明辨。」 Scanlon的哲學思想有一個重點,主張寬容地對待別人對事情的理性評價,但並不停留在「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人與人相處,一方面尊重對方有權依于自己的價值觀對評價事情和作出抉擇;另一方面是透過說理來溝通。 為自己的健康問責 在醫療上面,尊重個人自主已是共識,但延伸的一個「負責」問題也值得思考:若是有人對自己的健康問題採取放任態度,到一天終於出了大毛病,社會是否無條件地補貼他的醫療費用? Scanlon引述另一個論者Julian e Grand的主張,加以評析和改進。這主張是,「當個人的健康情況是取決於他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因素,那麼他理應負責 (支付) 她(因未適當自我照顧) 而衍生的醫療服務需要。」 在這一點,容易想到的情境是:一個肝臟功能已見異常的病人選擇繼續享受海量的美酒,到肝臟壞死了,可以合理地期望怎樣的公費醫療為他包底? Scanlon認為,Julian e Grand的主張太苛刻,道理上也說不過去。很多有風險的活動,例如賽車、滑雪,人們是可以選擇不玩,但一般人不會認為當他們出了事,不應該有機會獲得政府資助的醫療服務。甚至婦女懷孕也有已知風險,你不能說懷孕與否完全可以由個人決定,因此出了併發症也是個人的事。 他提出要區分對個人行為的「怪責」(blameworthiness) 與「問責」(accountability) ,尤其是如果問責的結果是扣減政府對個人醫療需要的承擔。怪責是道德上的,即使很合理,也不代表可以完全抹掉政府或社會對他患病時的施救責任。 他提出比較溫和的主張:病人選擇的生活方式(例如喜歡高危運動)只是引致患病後果的一系列複雜因素之一,不能說,你的重病完全是自招的,理應自付醫療費用。另一方面,無論個人的選擇權有多重要,因為醫療費用要由承擔,社會應否對不同風險活動的醫療後果一律承擔,公眾有權作出衡量。 […]
The 2nd Asia Pacific Bioethics Education Network (APB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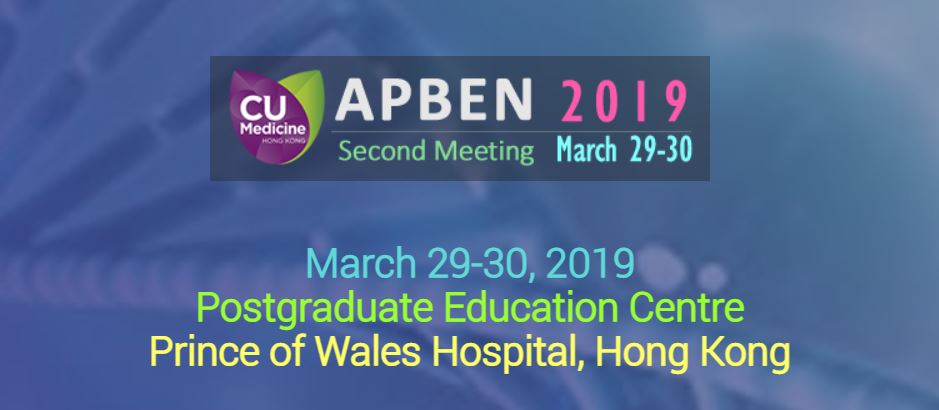
Date: 29 – 30 March 2019 (Friday – Saturday) Time: 9:00 a.m. – 5:45 p.m. (Day 1) ; 9:00 a.m. – 1:00 p.m. (Day 2) Venu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entr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Programme Details: https://webapps.med.cuhk.edu.hk/apbpmed/APBP/2mtg/index.html To re-visit the lecture videos and powerpoint slides, please click here (see “lecture videos & ppts”).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 of APBE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