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Club: From Bioethics to Biopolitics: the Case of CRISPR

Date: 16 November 2017 (Thursday) Time: 5:00 – 6:30 p.m. Venue: Room 211, 2/F, Cheng Yu Tung Building, CUHK Campus, Shatin Speakers: Prof. Rob Sparrow,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Dr. Catherine Mills, Associate Professor, Monash Bioethics Centre,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Event Recaps: Presentation slides by Prof. […]
Genome Editing and Human Equality

Date: 10 November 2017 (Friday) Time: 4:30-6:00 p.m. Venue: Room 308, 3/F, Esther Lee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5-8 mins walk from the University MTR Statio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Prof. Robert Sparrow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Flyer: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Presentation slides by Prof. Robert Sparrow – “Genome Editing and Human Equality”
器官捐贈倫理:香港的斟酌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6.11.2017)

器官捐贈倫理:香港的斟酌 在生命倫理學,器官捐贈與器官移植捐贈是大題目,其中又有性質各別的「細」議題。這些議題在公共空間時冷時熱,今年四五月間,由一個不幸的鄧女士換肝個案掀動熱烈爭論。鄧女士個案有很多傷口,這兒不擬再具體談論,但是由之帶出的一項爭議,即《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行政指引硬性規定所有在生器官捐贈人必須年滿18歲,是否太過嚴厲,就納入了政府有關器官捐贈的公眾諮詢範圍當中。 立法會在6月14日討論這個題目,食物及衛生局提供了一份《有關器官捐贈及移植的背景資料》(下稱《文件》),寫得清楚持平,值得細讀。它包含三個議題:一、應否降低活體捐贈者的合資格年齡(至18歲以下);二、可否試行「配對捐贈」計劃,即配對兩個器官輪侯者,各自家屬交叉捐贈;三、香港應否採用「預設默許」(opt-out)的器官捐贈機制。 三個議題之中,配對捐贈其實並沒有甚麼倫理爭議,主要是做好交叉配對過程的 公平性,而且能向其他等候器官移植但未能交叉配對的病人清楚交待,就可實行。外國也有實際運作經驗可供參考。 活體捐贈者的合資格年齡應否降低至18歲以下,卻未必可以簡單照搬外國,儘管文件也羅列了各國的不同規定。外國規定有寬有緊,背後與當地怎樣看青少年的自主年齡和法定年齡應是有關連的。 在今年四月鄧女士的個案,當時公眾很受她的女兒﹙年齡還差一點才符合活體捐贈的規定﹚的孝心和親情感動,有議員促請緊急修改法例降低年齡規定,記者訪問港大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簡尚恆教授,簡教授說自己經常和學生說「hard cases make bad law」,意思大概是,那些艱難的個案常常摻有複雜和獨特的元素,基於獨特個案去制訂影響深遠的法例,容易變得傾斜。 當日港大盧寵茂教授喝止緊急修例,有兩個理由:一是成年人捐贈器官還有很多推廣普及空間,不應向未成年的人士打主意;二是他團隊見過年輕子女(即使已滿18歲)在捐贈的決定上頗受長輩和親友的有形無形壓力,因此堅持需要保護未成年的人士。 《文件》討論這個問題,焦點在應否有酌情空間。筆者認同原則上不能排除18歲以下也可能有心智特別成熟的年輕人,但需注意活體捐肝者死亡率在千分之一至五之間(視乎摘取肝葉的大小),身心後遺症也有兩成多,在緊急決定捐肝救人的時刻,要評定一個年輕人心智成熟並已充份認知利害,難度很高。在最壞情況,如果病人接受了捐贈仍然不治,而未成年捐贈者亦不幸死亡,負責酌情的人難以釋然。 其實任何地方的器官移植主力都是靠遺體捐贈,捐贈文化良好與欠缺普及的地區(香港屬於欠缺普及地區)的器官捐贈率可以相差兩三倍。這也就是政府諮詢「應否採用預設默許器官捐贈機制」的由來。還是看國際經驗:「預設默許」會有幫助,但並非單方妙藥,還需配以有力和創意的推廣運動和病房溝通。 Prof. Martin Wilkinson是紐西蘭器官捐贈政策的學者顧問之一。上月他從英國返紐西蘭過港,生命倫理學中心請他來專題講「自願捐贈」(opt-in,即香港目前的制度)與「預設默許」取捨,卻原來他極力贊成「預設默許」,指出在香港目前的制度,即使生前未有登記捐贈,只要家人同意,死後一樣可以贈出器官,這其實與「預設默許」沒有什麼分別。他看關鍵在於家人仍可反對,「預設默許」就不會有大問題。 有人問,若果一個長者沒有家人,那麼「預設默許」又是否合理?他認為實際上適合使用的遺體器官很少來自全無親人的長者,釐清捐贈人士的條件,可在設計機制時處理。「預設默許」機制要公平合理,關鍵是要能容易拒絕和退出,以彰顯對個人意願的尊重。 科技能解決器官需求? 器官移植界一直面對著器官供求不足問題,要平衡病人的逼切需要和對捐贈者公平並不容易。未來生物科技能否徹底解決需求問題,甚至連倫理爭議也一併消失? 科學界致力研究細胞移植取代器官移植的可能性,希望以修復器官的方式減少對於捐獻器官的需求,近年有些眉目。科研人員利用幹細胞分化成各種細胞和利用組織工程將細胞重組成器官,得到初步成果。 日本東京大學醫科學研究所今年公佈,成功將小鼠的幹細胞植入大鼠胚胎生長出胰臟腺體,再植回糖尿病小鼠中使其血糖逹致正常水平。今年八月,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亦有研究人員成功開發出一種「組織納米轉染」(tissue nano-transfection)新技術在活體內細胞重組,希望生成不同的細胞類型,協助修復受損組織或恢復老化的器官、血管及神經細胞等組織。實驗室老鼠測試顯示,皮膚細胞能被重新編程成為血液不暢的傷腿中的血管細胞。在一周之內,活血管開始出現在傷腿中,三周後傷勢開始好轉。 雖然實驗室的成果得到肯定,但這些技術要在人體實踐始終面對重重挑戰,2010至13年間,瑞典卡羅琳學院的Paolo Macchiarini 將幹細胞培植的人工氣管移植到氣管受創的病人體內,九名受移植病人中有七名最後均告死亡。後來Macchiarini被指手術風險評估失當,而且在發表的文章中歪曲研究成果。事件最後令該院解僱Macchiarini,同時該院參與聘用Macchiarini的Urban Lendahl也辭任諾貝爾委員會秘書,而卡羅琳大學醫院行政總裁Melvin Samsom今年七月亦在《The Lancet》撰文承認Macchiarini當時使用的技術並未準備好用於病人身上。 儘管有科學上的道德陰影,技術層面的突破又尚需時日,學界對幹細胞和器官重組技術的突破仍然樂觀。如能在人體成功重組或修復複雜的器官,就有望紓解器官移植界的難題。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7年11月6日,C2 )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Programme 201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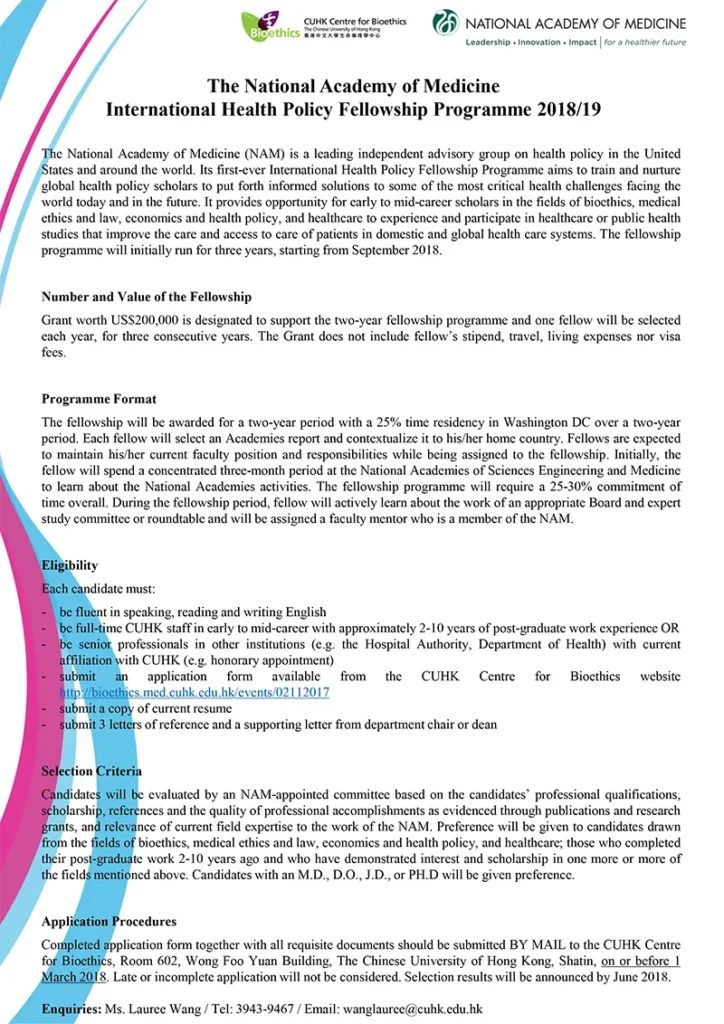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NAM) is a leading independent advisory group on healt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Its first-ever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Programme aims to train and nurture global health policy scholars to put forth informed solutions to some of the most critical health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 […]
Journal Club: Truth-telling in Medicine and Nursing

This event is by invitation only Date: 19 October 2017 (Thursday) Time: 5:00 – 6:30 p.m. Venue: Room LG 04, Hui Yeung Shing Building, CUHK Campus, Shatin Speaker: Dr. Jacqueline Yuen, Clinical Lecturer, Department of Medicine & Therapeutics, Faculty of Medicine, CUHK Discussant: Dr. Chun-Yan Tse, Chairman, Clinical Ethics Committee, Hospital Authority Event Recaps: Journals: Truth Telling in Medicine: The Confucian […]
人體試驗對象:誰是脆弱者?(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9.10.2017)

人體試驗對象:誰是脆弱者? 現代科研倫理(research ethics)對人體試驗管得很嚴格,這並非素來如此。話說從頭,多數人從二次大戰後1947年紐倫堡審判講起。23名德國醫生因在納粹集中營進行滅絕人性的人體「醫療」試驗,最終以「戰犯並違反人性」罪名受審,16位醫生判有罪,其中7個醫生被判死刑。之後,紐倫堡法典(Nuremberg Code) 誕生,其中第一條即強調,在人體試驗,「試驗參與者的志願與同意是絕對的根本需要。」 論違反人性,二次大戰日本731部隊在東北以活生生的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實驗,比納粹德國醫生的實驗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協會(NHK)播放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者與人體實驗》,才首次公布了731部隊認罪的錄音資料,並指多名日本醫學界權威專家曾涉入731部隊人體實驗。 戰爭泯滅人性並非常態,討論醫學科研的倫理,或者應以和平時期的「正常」研究為基礎。這樣的話,現代醫學研究的倫理醜聞,就應從上世紀美國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Service) 核准並且資助進行的Tuskegee梅毒研究講起。 這是一項縱向的長時期病變與病情觀察研究,1932 年至 1972 年期間在美國阿拉巴馬州 (Alabama) 的塔斯基吉鎮 (Tuskegee) 進行。研究最終導致 28 人死亡,100人傷殘,40受試者的配偶也感染梅毒,19名嬰兒因而染上先天性梅毒。 在1972年7月,華盛頓星報及紐約時報揭露醜聞,全民譁然。醜聞促使國會立法檢討人體研究的管控機制,也促使了1979年「貝蒙報告」(Belmont Report) 的誕生,報告特別針對醫學研究,提出倫理監管要求。其後美國建設機構審查會制度(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建立今日各國科研倫理委員會採用的規範格式。 為什麼美國公共衛生當局竟然會資助違反基本道德的研究?從體諒(不是原諒)角度看,在三十年代,梅毒是極可怕的疫症,面貌多變,致殘致命又無有效治療。研究起初是為長期觀察感染梅毒的病人,看病情如何發展,這屬於疾病自然史的研究範圍。問題出在四十年代,這時青黴素已經面世,梅毒可以治癒,研究人員卻擴大研究範圍,繼續免費醫療、食物甚至喪葬補助吸引貧窮的黑人參加,把他們分為兩組,一組給予青黴素治療;卻任對照組病人自生自滅,兼且欺瞞他們,說他們只是體內有「壞血」(bad blood) 需要研究,絕口不提梅毒,遑論有效治療。就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下,這201 名對照組病人得不到青黴素醫治,或死或殘,更禍延妻兒。 阿拉巴馬州梅毒病人與二戰集中營被強迫接受試驗的人群有沒有相似之處?明顯地,兩個時空的研究都沒有基本知情同意程序,受試者不由自主。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角度是:他們同是處於絕對弱勢的人群,任人魚肉。 這衍生了一個現代的觀念:做人體試驗,除了要求普遍性的知情同意,還須特別留意那些vulnerable的人群,特別細心保障他們的權利、安全和福祉。 Vulnerable population在內地譯為「脆弱人群」,台灣譯作「易受傷害族群」,比較準確。有些指引列出兒童、精神病患者、弱智人士、孕婦、囚犯及受機構監護人士、少數族裔等,作為「脆弱人群」的界定,但學者為此頗有辯論。有人認為這缺乏邏輯的一致性,當中一些是無自主決定的能力,但孕婦列入其中卻是為了怕胎兒容易受試驗的藥物的不良影響。把囚犯及受機構監護人士很容易理解,少數族裔是否自然入於「脆弱人群」之列就有些爭議?出於好意的保護會否變成標籤歧視? 保障「脆弱人群」變成障礙? 這問題經常有討論但不易簡單定論。以孕婦為例,如果因為生怕試驗對胎兒造成危害風險,一律不讓她們加入研究計劃做受試者,長遠而言相關的醫學和治療便停滯不前,個別孕婦受保障的代價是未來許多孕婦不能得益? 合理的研究指引都不會禁止以孕婦為人體試驗對象,但對試驗中的干預(例如藥物、侵入性的診斷方法)的安全性會有更嚴的要求,知情同意的過程必須披露對孕婦和胎兒的所有已知風險,而且風險與對他們的裨益必須相稱。 孕婦例子還較易處理,因為可以用嚴格的知情同意程序提供保障。認知障礙患者又如何?「老年癡呆症」是迫在眉睫的整體人口健康挑戰,研究開發醫學和護理新產品很有迫切需要,但除了非常早期的患者,知情同意程序並不適用。 台灣在2011年公布了「人體研究法」,教育部為此編印一本官方指引《人體試驗──研究倫理的理念與實踐》,其中一章以案例解讀實踐中的原則。有一個案例是這樣的:研究計劃擬納入20名中至重度失智症(老年癡呆症)老人及20名智能正常的老人進行腰椎穿刺(lumbar puncture),取腦脊髓液進行分析,以探討失智症的致病機制。IRB的審查意見是,本研究對受試者沒有直接利益,但卻有明顯高於微小風險之潛在併發症,故不予核准執行。 指引編者的剖析是,因為這些老人室是缺乏決定能力的易受傷害族群,必須受到額外的保護,代理決定者例如家人必須以受試者的權益和福祉為最優先考量,無權代失智老人同意參與風險高於利益的試驗。 但指引也在另一節提及,研究倫理原則要因時空變遷而不斷調整。如果人體研究的規範「獨尊」受試者的個人利益,禁止「拔一毛以利天下」,是否過當?作者說,「近年來對於研究的利益逐漸又返回往『社會利益』思考。」 新加坡的科研發展進取,在倫理原則方面樹立了一條有新加坡特色的Principle of solidarity(或可譯作「社會凝聚原則」),意思是,個人與群體利益在社會中相依存,研究若關乎群體利益,即使對受試者個人並無好處,亦應考慮允許進行。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7年10月9日,C2 )
Opt-out Donation and The Ethics of Organ Retriev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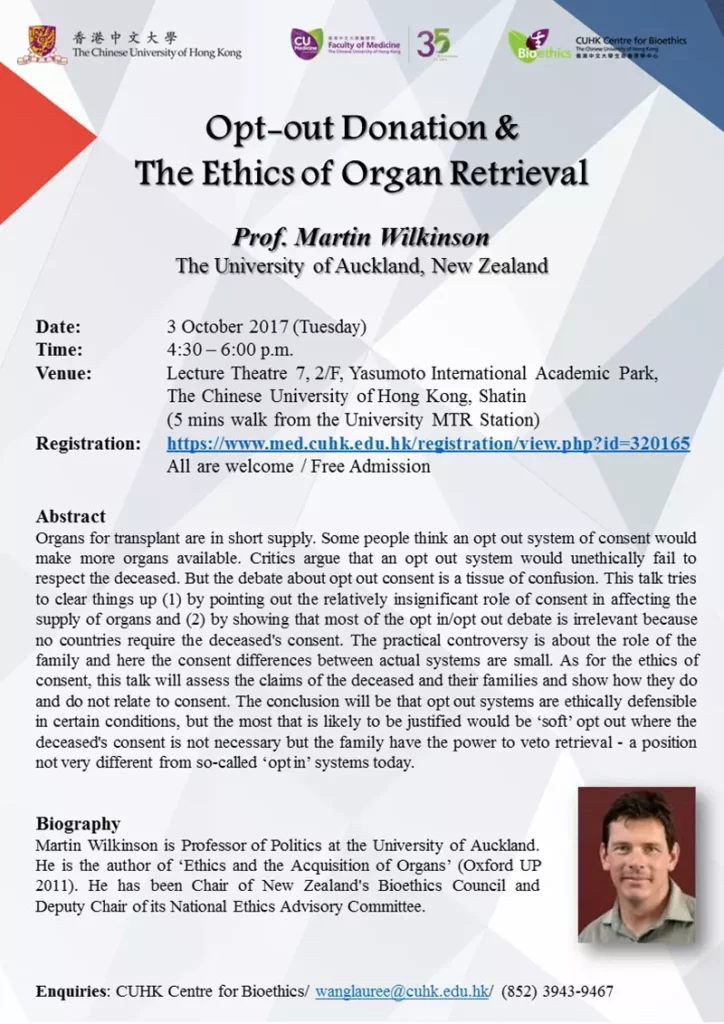
Date: 3 October 2017 (Tuesday) Time: 4:30-6:00 p.m. Venue: Lecture Theatre 7, Yasumo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Prof. Martin Wilkinson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Flyer: Please click here
Journal Club: 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Brain: Questions on Personhood, Patient Autonomy and Patient Rights

This event is by invitation only Date: 21 September 2017 (Thursday) Time: 5:00 – 6:30 p.m. Venue: Room LG 04, Hui Yeung Shing Building, CUHK Campus, Shatin Speakers: Dr. Derrick Au, Director,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Dr. Gilberto Leung, Clinical Professor, Academic Neurosurgeon, Li Ka Shing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vent Recaps: Journals: “Psychosurgery and […]
免於「被急救」 台港大不同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1.9.2017)

免於「被急救」:台灣與香港對晚期病人的保障 台灣在2016年1月公布了《病人自主權利法》,將於2019年實施。此法例爲「預立醫療決定」 (香港稱爲「預設醫療指示」) 確立了法律效力,大大改進了台灣晚期病人對維生治療的抉擇權。台灣這一次法律改革,是有其獨特背景的;香港近年亦漸見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的討論,陸續有病人使用。對照兩地,可以比較清楚地見到其中的倫理問題和法律考量。 關鍵的倫理焦點是:現代醫療科技發達,即使疾病已到晚期,很多時還可以用維持生命治療(以下簡稱「維生治療」)延長生命。到病人病危,提供人工呼吸,心肺復甦術等「急救」 程序是基本常規。問題是,若疾病本身不能逆轉,「急救」只是延長死亡過程,不單增加病人痛楚,更可能是沒有意義,甚至損害人格尊嚴。尊重病人自主既然是重要的倫理原則,那麼病人理應有話事權,拒絕接受對他們無意義的維生治療,包括免於「被急救」。問題是:病人能「話事」嗎? 台灣《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法案提案人是立法委員楊玉欣。她接受網上《康健》雜誌訪問說,「我們平常可以決定吃什麼、穿什麼、決定跟誰結婚,為什麼變成病人就失去了自主權?常是醫生、家屬替病人決定,病人的意願很少有機會表達,遑論受到尊重。」她推動法案,除了希望確保病人有知情、選擇與決定醫療選項的權利,也是鼓勵民眾提早思考,當病情變成「賴活不如好死」的狀態,會怎樣選擇? 楊玉欣委員和丈夫孫效智教授曾於2015年12月到香港醫管局交流。在簡報中,他們解釋,台灣固有法律(包括醫療法60條、及醫師法21條規定,加上刑法第275條及第15條) 的指導原則是「保護生命寧過勿不及」。醫生有法律責任為危急病人「急救」。2000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以及之後的後續修法,賦予末期病人選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治療的權利,2011年的修訂,亦容許不清醒末期病人的家屬訂立同意書不要維生治療。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保障始終限於末期病人。 最新的《病人自主權利法》,透過「預立醫療決定」,把病人抉擇權擴展到不屬末期的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疾病,包括:(一)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二) 永久植物人狀態;(三) 極重度失智;(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法例在2019年才實施,即是說,在此之前,一個晚期病人患上嚴重不可逆轉的疾病,只要未到末期,即使病人及家屬反對,醫生也要「依 法急救」。病人沒有「話事權」。 香港的有關法律情況,與台灣很不同。整體來説,香港沒有針對醫生的、類似台灣 「保護生命寧過勿不及」 的法律,病人對免於被「急救」 有較多話事權。 首先,雖然香港未有爲 「預設醫療指示」 立法,但是跟據普通法,有效和適用(valid and applicable)的「預設醫療指示」 具有法律效力,醫護人員須要尊重。醫管局使用的 「預設醫療指示」 表格,涵蓋了末期病人、持續植物人狀況或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況,亦包括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受限疾病(other end-stage irreversible life-limiting conditions)。 香港對入侵性治療(invasive treatments)的法律觀點跟台灣更是迥異。在香港,無論病情在早期或晚期,若病者是成年而且神志清醒,必需要病人知情同意,才可以提供治療,包括維生治療。如果病人神志不清醒,不能簽署同意書,又未有預設醫療指示時,醫生會跟據香港的《精神健康條例》,為病人提供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治療。考慮病人的最佳利益,必須要衡量該治療對病人好處(benefit) 與負擔(burden) ,這涉及病人的價值觀。故此,要為神志不清醒病人作出決定前,並不會簡單地假設急救好過不救,應考慮病人曾否事先表達有關治療的意向,經醫護人員與病者家屬商討,尋求共識。 因此,在香港,即使病人沒有簽署預設醫療指示,又即使疾病未到末期,如果病情已屬嚴重不可逆轉,醫護人員與病人家屬同意「急救」是不符合病人最佳利益和意向,醫生不作「急救」也不會像在台灣那樣跌入刑責法網。 加上引號的「急救」 寫這個題目,全篇都要特別用引號把「急救」一詞括起來,因為當「急救」完全不符合病人的利益和意向,那只是行禮如儀的動作,沒有治療意義。 在法律得到改革之前,台灣的醫生迫於無奈依 法「急救」;香港的法律比較合理,有空間讓醫生考慮病人的最佳利益和意向,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的法律條文完全不須改進。 一個需要正視的法律問題在《消防條例》第95章第7條,其中規定救護員有職責「用以下方法協助任何看似需要迅速或立即接受醫療護理的人─ (i) 確保該人的安全; (ii) 令該人復甦或維持其生命; (iii) 減少其痛苦或困擾;」 這第(ii) 項在執行上變成無論運送的病人是否末期病人也必定要「急救」,即使末期病人已簽署「預設醫療指示」 反對心肺復甦術,亦有醫生在 文件上清晰表示病人的指示屬有效和適用,救護員仍會爲病人做完全無效用的心肺復甦術,進行所謂「急救」。對於這些末期病人,「被急救」只會帶來完全不必要的痛楚。《消防條例》這條文比台灣 「保護生命寧過勿不及」的法律更僵硬,須儘早正視。 醫管局在2002年已訂立維生治療的指引,在2010年進一步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指引,在2014年更新「不作心肺復甦術」指引時,更把涵蓋範圍擴展至非住院病人。本文作者一直有參與其事。雖有指引,前線醫護人員執行時仍面對一些困難。如果法律能夠配合,培訓得宜加上公衆教育,香港很有希望大大改善對晚期病人的保障和照顧。 原載 […]
Journal Club: Moral Distress in Nursing

This event is by invitation only Date: 10 August 2017 (Thursday) Time: 5:00 – 6:30 p.m. Venue: Lecture Theatre 4, 2F, Cheng Yu Tung Building, CUHK Campus, Shatin Speakers: Dr. Derrick Au, Director,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Dr. Helen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Nethersole School of Nursing, CUHK Event Recaps: Journals: “Moral Distress in Nursing – Coping with this ris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