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心」「共享」消失之後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9.12.2019)

這篇文章是在紐西蘭南島南端的城市鄧尼丁寫的,寫時理工大學的圍困還未解。早一星期我離港時,圍困爭持激烈,街上聚眾聲援,警方以催淚彈驅散,連伊利沙伯醫院也受到波及。抵達鄧尼丁,為我辦理入住旅館手續的是一位衣著整齊、談吐斯文的先生,禮貌地問我來參加什麼會議,我說關於法律和倫理。他又問我從哪裡來,聽到「香港」二字,就敏捷地反應道:「那你一定有很多法律和倫理問題可談了!」其實我來是談香港最近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的公眾諮詢。這位接待的先生似乎很清楚香港的困境,輕輕說:「雙方堅持不退讓,就沒法解決了。」我後來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律師。 這篇文章刊出時,慘烈的鬥爭已經持續了整整半年,期間許多既有的價值規範嚴重破損。有人哀嘆香港回不去了,甚至說,this is the end of Hong Kong as we know it。 可是,我們熟悉的和惋惜的香港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選擇惋惜什麼,不完全是客觀的,往往反映自己最著緊的是什麼。本報同文「天峰醫生」是我以前的醫管局同儕,近月接連兩篇專欄文章談「烏合之眾」。這是從一本暢銷書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出發,剖析為什麼原本會思考的「個體」聚集變成「群眾」之後,容易情緒躁動,變得愚蠢盲動,不問手段。我覺得他是在惋惜香港失去溫和理性。我卻也覺得,「烏合之眾」的鏡子同樣應該照向另一方。同文雖然也有批評政府在處理危機上欠決斷,但就沒有注意到,當整個政府與警隊自我綑綁,同樣形成了遠比「個體」愚蠢甚至盲目的「集體」。The unpopular mind和the popular mind一樣偏執。 「齊心一意」甚難 我還未決定自己最惋惜的是什麼。在鄧尼丁的會議我參加了一個工作坊,小休時有與會者問及香港的抗爭情況,我只能簡略地說來龍去脈,再補上一點感想:過去香港人互相容忍不同的價值觀,雖然未必好好對話,總算有兼容的空間,現在沒有了。 晚上我上網搜尋了一下過去十年間香港普遍流行什麼願景口號,其中兩個特別明顯:「齊心」和「共享」,分別見於兩屆特區政府新上任的時期。2012年新行政長官梁振英就職致辭,以「齊心一意,共建香港」作為主題。當日他說:「只要我們齊心一意,必定能夠將香港打造成兒童茁壯成長、青年實現理想、壯年人一展所長、長者安享晚年、七百萬市民安居樂業的理想家園。」這聽來容易,其實難於登天。「只要」是以全民一致為大前提,這有什麼可能發生?香港社會並不是一個傳統的儒家大家庭,即使當它是個大家庭也要正視家庭內的嫌隙不和吧。試想為什麼香港一向要標榜包容?因為這本就是一個多元化、習慣了歧異、思想自由的地方。當然自由並不是絕對的,提倡「齊心」也並無不可,但是不宜一味排斥異質;即使有些事情要劃紅線,也不宜以打擊異類作為施政主軸。 社會分崩離析時,卻還見有報章社論十年如一日地呼籲大家要齊心協力,覺得諷刺。早在這個十年的開頭,和諧團結同坐一條船的想像已在消散。香港人齊心的感覺,往回溯已是2003年沙士抗疫,2008年汶川大地震也曾喚起民胞物與的中港情,之後就每況愈下。來到今天,在這個十年最後一個月回頭看,只不過半年,所有對抗牴觸、異化疏離的情緒都夾著憤怒決堤泛濫。這是互動互撞形成的,不能以「群眾如何變得愚蠢」簡化地去理解。 「共享」忽略矛盾 現屆政府沒有侈言「齊心」,改用了「共享」理念,土地政策談共享,學校也在教育關懷共享。「齊心」和「共享」兩者雖然同樣建立在一種和諧的想像上面,但相較之下,「齊心」貼近中國傳統文化,「共享」較有些現代色彩。 政府沒有政治顧問,對香港深層矛盾的分析很少,「共享」的概念就侷限於民生經濟範疇,著眼於市民未能分享社會富裕的果實。順此思路,也就假設青年因無法置業,在社會無根,容易成為失意反叛的青年。其實儘管市民普遍也希望居有其所,房屋問題並不是矛盾的癥結。人們可能在尋找有意義的參與,在參與中建立身份認同。然而在官方話語中,「人心回歸」本身就是終極的意義和身份。 近五、七年間,環繞「自由」和「歸心」的政治角力鬥爭主導了社群的互動,香港公民社會本就不多的人文精神日呈萎縮。本來,政治疾風吹得越勁,社會就越需要建制內外(這是泛指social institutions,不是狹義「建制」) 的知識分子頭腦清醒,堅守專業精神、珍惜規章制度和人文價值;可是在發熱的鬥爭中,這一切都把持不住。 當對抗落幕,我們必定要面對百廢待舉的香港。「齊心」「共享」願景已經破碎,政治口號或者陸續有來。香港需要包容夢想,夢想需要尋找切實的基礎。未來香港的願景要透過開放式的互動共同搭建。我們理應視彼此為真實共存共在的人,堅持誠實正直開放,一步一步前行。
[Postponed!] Workshop on “Choice and Care near End of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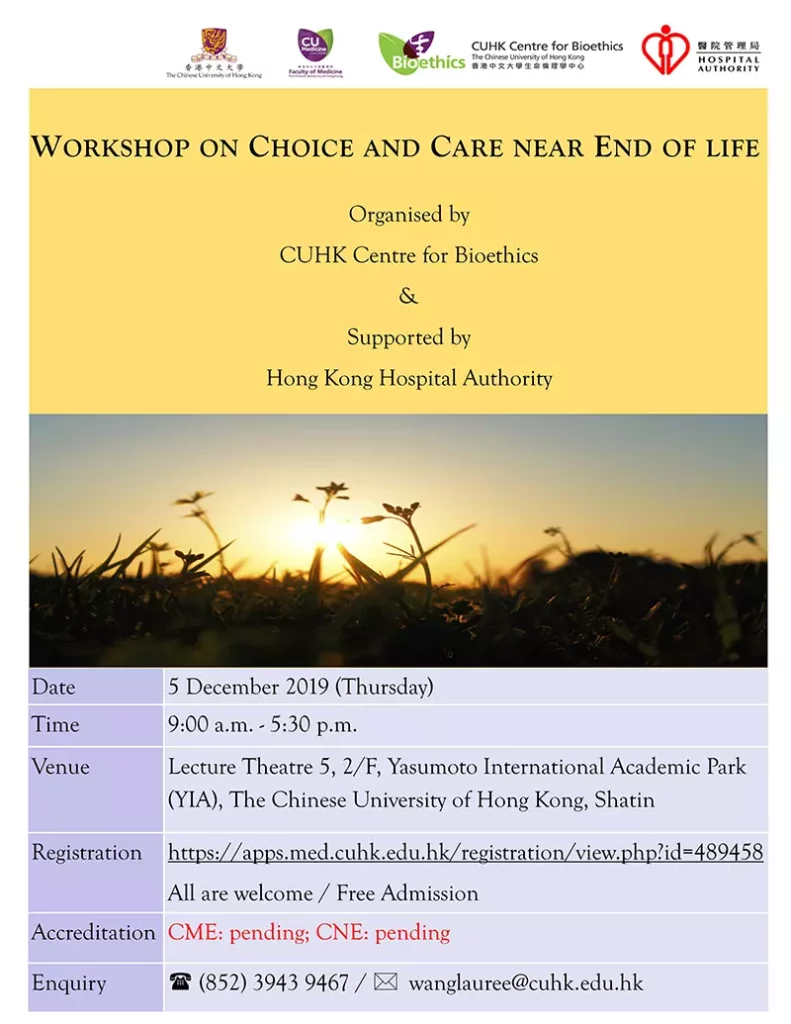
Please note that the workshop has been postponed to March 2020.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once availabl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Date: 5 December 2019 (Thursday) Time: 9:00 a.m. – 5:30 p.m. Venue: Lecture Theatre 5, 2/F, Yasumo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Programme Rundown/Poster: Please click here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The workshop […]
生物庫、知情同意與公益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1.11.2019)

香港劫難未過,社會撕裂之外,公眾對政府的基本信任也在快速蒸發。近例是食物及衞生局長在電視訪問中解說,催淚彈對身體造成不適僅是短暫,水炮車的顏色水劑亦是無毒,大多數市民人若非完全不信,也會覺得這是對公共健康風險的輕描淡寫。此時期,食衞局一些重要的政策事項仍在推進,祈盼社會公眾有成熟的就事論事的底子去看待。事項一是9月初食物及衛生局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向公眾諮詢;事項二是年初成立的基因組醫學督指導委員會近期完成了階段性工作,將就發展路向提出建議。我在兩個事項都有些機會直接或間接地提供一些意見。本文針對後者基因組醫學範圍的生物樣本庫(biobank,簡稱生物庫) 題目,談「知情同意」的問題。 建設生物庫在過去的20年間成為熱潮,各國視之為科研與創新的基礎建設。把生物樣本儲藏起來,供日後分析、研究和其他用途,不是新事物,當基因組學(Genomics) 興起,人體組織生物庫與大數據概念結合,政府與企業的投資規模越來做越大。這些生物醫學與生物科技範疇的事情本來離開普通人很遠,但在很多國家也是社會關注的倫理議題。醫學科研要求合理的知情同意,這是以尊重個人權利為基礎。近年有些討論在問:個人權利為本之外,可否也考慮社會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 ,把傳統的知情同意模式放寬? 核心問題 核心問題是採集和儲存人體組織樣本和資料,供研究者共用,必然涉及獲取「知情同意」。舉例說,醫治癌症病,幾乎百分百需要採集腫瘤組織,供組織學診斷;現今治療腫瘤,又常會進一步做基因測試,更為精細地分類和設計標靶治療方案。這是為了病人本身的治療需要,並沒有特別複雜的「知情同意」問題。設想一個醫療或大學機構每年收集數以百計的腫瘤組織樣本,如果每個病人治療完成後就把樣本丟棄,這豈非極大的浪費?因為隨著科學進展,與病人醫療資料相連的組織樣本,日後很可能有切實的科學研究和科技開發的價值。如果病人能理解這個有點近似捐贈的概念,為了未來病人的利益而同意機構儲存樣本,開放性地用於研究,這就是「共同利益」概念。本文標題選用了更寬的「公益」字眼,可能較容易理解。 具體的難處在於,一旦涉及科研和收集個人資料,就得嚴格地合規合法。傳統的「知情同意」概念是,我參與一項研究,需要知道這研究對我有何風險、得益或損害。我同意的參與一項研究,不等於同意參與它引伸的所有附帶研究,以至一些目前連概念都未有的研究。如果涉及例如個人基因的資料,感覺上就更為敏感。再進一步,生物樣本庫可能是未來生物科技產業的引擎,最終可能牽涉商業利益,這又多了一層考慮。 中間落墨 在傳統的「知情同意」與全開放性的捐贈概念之間,有很多中間落墨的方案在各國試行。去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檢視了20個國家的生物庫的做法,確定了有12個國家決定採用某種形式的「廣泛同意」(broad consent) 程序。 Broad consent是否應一律譯為「廣泛同意」我還不太肯定,因為視乎同意的範圍有多大,日後的應用有多開放,它可以是比傳統的知情同意較為寬廣,也可以是十分廣泛,不能一概而論。 從保護個人權利的角度出發,以共同利益作為要求個人犧牲的理據不是沒有爭議的,因為在政治範圍,政府可能把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作為藉口管制人民的行為。有些公共衛生措施沒有爭議,例如強制司機和乘客使用安全帶。在器官捐贈方面,年前政府曾諮詢公眾,香港可否改為實行「默許同意」(opt-out) 制度,即生前若無表示反對,就視為同意在死後捐出器官。我個人傾向有條件支持「默許同意」,但諮詢結果是有爭議,最終沒有推行。 與生物庫有關的知情同意問題並沒有捐出器官那麼嚴重,broad consent比起opt-out溫和得多,但我看broad consent仍然是要有條件的,那是必須建立一套良好可信的管治(governance)制度,不能任由生物庫的發展讓市場主導,機構不能在黑箱中作業。 世界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正在編寫《關於健康資料庫和生物樣本資料庫倫理考慮宣言》。它的思路是生物庫要考慮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建立有關生物樣本資料庫應符合通用的標準,有品質管制,和對公眾負責。這似乎也是傾向於以良好規範和良好管治取信於公眾。 參閱: M. A. Rothstein, H. L. Harrell et al. Broad Consent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RB: Ethics & Human Research, the Hastings Center, Nov-Dec 2018; https://www.thehastingscenter.org/irb_article/broad-consent-future-research-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 雷瑞鵬、馮君妍:〈生物樣本資料庫的泡沫已經破裂了嗎?〉, http://kuaibao.qq.com/s/20180529G1AHOD00?refer=spider,轉載自《醫學與哲學》2018年第5期。
青少年能有多自主?(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4.10.2019)

青少年能有多自主? 青少年在作出關於自己的重要決定時,能有多大的自主權?對上一次我較為仔細地看這個問題是在兩年多前,當時香港社會在辯論應否放寬法例規定,以容許一名不滿18歲的少女捐贈活體器官給不幸急性肝衰竭的母親。當日社會的主流情緒傾向於同情,認為應該酌情容許例外。那還不止是一種情緒,人們是判斷少女心智成熟有如成人。數字上的年齡是死的,青少年的心智成熟可能因人而異。兩年之後的今天,香港處於凶猛的政治對抗之中,好像給送到另一個宇宙時空。今天來問同一問題:「青少年能有多自主?」情境完全不同了。 香港有保護兒童包括少年的傳統。保護兒童的法例反映了這一點,例如針對青少性行為有最低的合法年齡的規定,與16歲以下的兒童性交是刑事罪行,不可以解釋說這個15歲的少年特別成熟,有能力自主同意。 香港沒有統一的法定年齡。同意性行為的最低年齡為16歲,成人身份證在18歲時發放,但未經父母同意的合法結婚年齡為21歲。 法定年齡不一 法定年齡不一未必是不合理。青少年的自主能力不宜抽空地看,要考慮所作的決定有多複雜和有多大影響。年輕人年滿18歲就可以投票,但21歲或以上才能競選議會席位。邏輯很可能就是,議政是關係重大的,有較高的年齡要求不算不合理。當然也還可以爭論,為何訂在21歲? 有些法定年齡的差異不大合乎邏輯。例如青少年16歲可以同意性行為,但購買香煙和酒精的年齡為18歲。難道買香煙比性行為更嚴重? 更矛盾的年齡界線還有:法例容許年滿15歲從事全職工作,年滿13歲就可以兼職工作,但是少年卻不准「獨留在家」,否則父母可能被控疏忽照顧。邏輯在哪裡?難道在家比出外工作更危險?抑或是少年根本不適宜獨處? 在醫療方面,對青少年的自主也有規定,層次較多,但最少在邏輯上有一致性。一般來說,香以18歲分界,但不是絕對界線。醫務委員會《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守則》)這樣規定:「十八歲以下兒童給予的同意屬無效,除非該名兒童能明白所建議治療的性質和影響。如該名兒童未能明白所建議治療的性質和影響,必須取得兒童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同意。」(第2.12.1條) 這是先劃定一條界線,在界線之下再予例外處理的空間。 英國早在1969年的家庭法案改革把未成年人士自己做醫療決定(例如簽署手術同意書)的界線從18歲放寬至16歲。香港並沒有跟隨。為什麼?我看香港社會仍有相當程度的傳統中國文化觀念,認為孩子普遍是不成熟的,需要依靠父母出主意。父母作為家長常在監察孩子,不大願意他們學習自主,怕孩子離開自己的監察範圍很容易「學壞」。 這反映在大人稱呼青少年的用語上。青少年不是青少年而常是「小朋友」,廣東話更會叫他們做「細佬哥」或「細蚊仔」。最近我見有大學校長與大學生對話時,全程稱呼他們為「同學仔」,而學生們似乎習以為常,起碼是不以為忤。 界線以下空間 當年社會爭論,那位少女只差幾個月就滿18歲,為何也不能簽署手術同意書?捐出活肝是一項手術,上述的醫務委員會《守則》豈不是寫明了,十八歲以下兒童如果能明白醫療步驟的影響,又得到父母同意,就可以同意進行手術嗎?純在法律角度考慮,這是因為《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是成文法(statutory law) ,當中對18歲的規定是絕對的,不像一般治療的手術那樣有18歲以下的例外和空間。在道理上,活體捐贈器官肝手術並不是一種治療,手術對捐贈者有健康風險(而且不低) ,但沒有健康上的得益。 香港醫務委員會《守則》對18歲以下青少年的醫療同意自主權利留有餘地,應是參照了英國一個稱為「吉利克能力」(Gillick competence)的法庭判案概念。在1985年Gillick v West Norfolk AHA一案,斯卡曼大法官(Lord Justice Balcombe)在判詞提出:「(雖然法例規定自主決定接受醫治的年齡為16歲) ,16歲以下的孩童(也)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受醫治,只要該名孩童有足夠的智慧,能夠並已經充分了解即將在他身上進行的醫療行為。」香港的年齡界線是18而非16歲,但邏輯和道理相同:在界線以下也需要個別考慮。因此,在香港的醫療實務中,16至18歲之間的青少年遇上重要的接受醫治的決定時,醫生會徵詢他們的意願,而非由父母決定。 近日筆者在想,那些每到週末走在街頭抗爭的青少年看來很有主意,完全不是大人心目中的「小朋友」樣子,這難免令大人疑惑失措:政治險惡,青少年能有多自主?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他們真的充份理解被逮捕和被投入監獄或少年教導所是什麼樣的後果嗎?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答案其實牽涉實證(而非個人意見) 。無論如何,我覺得評論者都不宜過多地將運動浪漫化,因為事情越複雜,情境越凶險,所作的決定影響越深,對青少年自主的心智要求也越高。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physician-diagnosed hypertension widened and persisted among women from 1999 to 2014 in Hong Kong.
機構有病,員工吹哨?(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9.9.2019)

機構有病,員工吹哨? 在臺北一個生命倫理座談上,我們從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案例談到研究人員的失德行為,以及倫理教育的重要性。然後,我們討論為什麼單是倫理教育並不足以規範專業道德。一位來自愛丁堡的講者深思熟慮,輕聲提出一個問題:在你們的醫療體系中,最困擾醫生和護士的道德兩難處境(ethical dilemma)是什麼?我馬上想到,在香港的公共醫療,這一定與人手和病床資源有關:醫護人員內心掙扎,不能提供真正優質的照顧。她說,在英國的衛生服務調查中,最令醫生和護士掙扎的道德兩難常常 是:工作中遇見不公與失德的事,要不要主動「吹哨」(whistleblowing) 揭發? 她的意思是,任何機構都有害群之馬,問題是為什麼不當行為容易被忽視?單靠倫理教育不行,要讓毛病呈現出來,才可改進。不當行為可能是隱蔽的,並不常是昭然若揭;當然有時也是因為機構選擇對它們視而不見。光是教育員工做正當的事是不夠的,人性不全是正直。機構應該為人員建立一種安全感,可以直言不諱地反對不良行為,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挑戰上級的權威,質疑機構的主流文化。 這是一個絕不簡單的問題。從實際角度考慮,機構很難無條件地鼓勵員工的吹哨行為。機構爆出醜聞總是令人尷尬,有時嚴重損害公眾信心。而且,管理層會想,人誰無過?如果員工不斷互相挑剔指責,有什麼看不順眼就告密檢舉,軍心動搖怎能作戰?大局為重,難免有時要護短,不能讓內部鬥爭絆手絆腳。有些管理層心知,鬆散和不規矩的行為在艱難的操作環境中也是潤滑劑。如果一切都要依足程序的話,繃緊的員工會不會受不了? 吹哨甚艱難 從倫理角度考慮,員工要作出決定吹哨,揭露黑幕,即使在合理的機構中也是充滿掙扎,甚為艱難。有兩種價值觀是互相衝突的:一邊是公平正義,一邊是傳統的忠誠。中國人的文化在往往對人不對事,把忠誠看得特別重,告密的人是「金手指」。還有更多貶損名詞:「二五仔」、「篤背脊」、「篤灰」,全都會令人不齒。這背後也有一重中國文化脈絡:歷史上的政治告密常是挾帶著惡劣用心。人們怎能假設吹哨告密的人全是秉持公義,絕無私心私怨? 因此,從忠誠的價值觀出發,檢舉是痛苦的決定,尤其是所揭露的事情是指控自己的機構正在損害公眾利益。如果大多數同事也是把機構的利益放在前面,公眾利益放在次要,那麼吹哨者就可能承受排擠、解僱,甚至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的後果。 2003 年沙士期間,蔣彥永醫生向媒體揭發中國沙士感染情況遠比官方數字嚴重, 這促使中國政府與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合作,令疫情得以控制。他在解放軍總醫院工 作,有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階,但後來仍受到很大的壓力,有消息指他一度被監視居 住。 在國際新聞,最知名的「吹哨者」當然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他因揭發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電子監聽計劃而被美國政府通緝。違反國家安全局的保密規定是刑事罪行,但是多數公眾認為他做了一件正義的事。網媒有文章以此為話頭,指出「斯諾登曾在香港匿藏近一個月;但諷刺的是,香港並沒有專門法例為吹哨者提供保障。這與國際的趨勢大相逕庭。」(〈訂定「吹哨者」揭密法 保障公眾利益〉,「評 台」,25/12/2016。) 立法保護吹哨者? 文章列舉,美國 1989 年的「揭弊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強調禁止報復,機構要建立進行調查的機制,與處理吹哨者一旦被報復的申訴機制;2015 年 5 月台灣通過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明確提及應保護檢舉人。在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曾草擬《2016 年公共利益披露條例草案》,提出應保護因公眾利益而披露資料的僱員,讓僱員毋須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禁止僱主解僱或歧視。這草案最後在立法會不了了之。 斯諾登與蔣彥永醫生的吹哨事件都是特大的事件,一般機構例如醫療機構面對的挑戰未必是特大黑幕醜聞,更多的是有沒有容忍慣常的專業不良行為,例如欺凌同 事、疏忽病人;有沒有大事化小,讓不良行為成為常態。每次出現「害群之馬」都是一個警報,提醒機構要審視既有的工作文化。要提防:「害群之馬」未必是單獨行 事。 我在醫院管理局工作時,曾參與討論如何制定可行的舉報政策。這很不容易。 如上述,對被舉報的人員公平也很重要,界定具體的檢舉是否關乎公眾利益也要合理。 一點觀察是,在現實管理中,一家醫院(或一個部門)如果保持開明態度,聽取批評和回饋時不是先行護短,那麼員工反而較少需要訴諸告密。 在管理上階級分明的威權文化,言路不暢,員工反而更多地通過匿名管道舉報而糾纏不清。有些文獻認為, 「吹哨」的定義其實可以從寬:員工敢公開提出關注,促進改革,也可以視為「吹哨」。善意的吹哨應該鼓勵。
人工智能武器誰負責?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2.8.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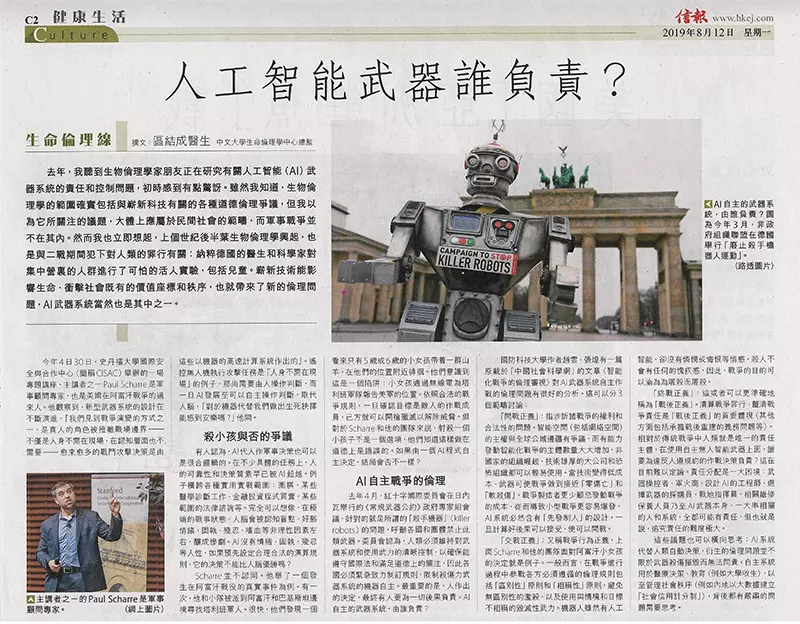
人工智能武器誰負責? 去年,我聽到生物倫理學家朋友正在研究有關人工智能(AI)武器系統的責任和控制問題,初時感到有點驚訝。雖然我知道,生物倫理學的範圍確實包括與嶄新科技有關的各種道德倫理爭議,但我以為它所關注的議題,大體上應屬於民間社會的範疇,而軍事戰爭並不在其內。然而我也立即想起,上個世紀後半葉生物倫理學興起,也是與二戰期間犯下的對人類的罪行有關:納粹德國的醫生和科學家對集中營裡的人群進行了可怕的活人實驗,包括兒童。嶄新技術能影響生命、衝擊社會既有的價值座標和秩序,也就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AI武器系統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4日30日,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 (簡稱CISAC) 舉辦的一場專題講座,主講者之一Paul Scharre是軍事顧問專家也是美國在阿富汗戰爭的過來人。他觀察,新型武器系統的設計在不斷演進,「我們見到戰爭演變的方式之一,是真人的角色被推離戰場邊界 ——不僅是人身不需在現場,在認知層面也不需要 —— 越來越多的戰鬥攻擊決策是由這些以機器的高速計算系統作出的。」遙控無人機執行攻擊任務是「人身不需在現場」的例子,那尚需要由人操作判斷,而一旦AI發展至可以自主操作判斷,取代人腦,「對於機器代替我們做出生死抉擇能感到安樂嗎?」他問。 依程式射殺一個小孩? 有人認為,AI代人作軍事決策也可以是很合邏輯的。在不少具體的任務上,人的可靠性和決策質素早已被AI超越。例子橫跨各種實用實戰範圍:圍棋、某些醫學診斷工作、金融投資程式買賣,某些範圍的法律諮詢等。完全可以想像,在極端的戰事狀態,人腦會被認知盲點、好勝情緒、固執、殘忍、嗜血等非理性因素左右,釀成慘劇。AI沒有情緒、固執、殘忍等人性,如果預先設定合理合法的演算規則,它的決策不能比人腦優勝嗎? Scharre並不認同。他舉了一個發生在阿富汗戰役的真實事件為例。有一次,他和小隊被派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尋找塔利班軍人。很快,他們發現一個看來只有5歲或6歲以小女孩帶著一群山羊,在他們的位置附近徘徊。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小女孩通過無線電為塔利班軍隊報告美軍的位置。依照合法的戰爭規則,一旦確認目標是敵人的作戰成員,己方就可以開槍殲滅以解除威脅。但對於Scharre和他的團隊來說,射殺一個小孩子不是一個選項。他們知道這樣做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如果由一個AI程式自主決定,結局會否不一樣? 去年4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行的《常規武器公約》政府專家組會議,針對的就是所謂的「殺手機器」(killer robots)的問題,呼籲各國和團體禁止此類武器。委員會認為,人類必須維持對武器系統和使用武力的清晰控制,以確保能遵守國際法和滿足道德上的關注,因此各國必須緊急致力制定規則,限制殺傷力武器系統的機器自主。最重要的是,人作出的決定,最終有人要為一切後果負責。AI自主的武器系統,由誰負責? 審視AI自主戰爭的倫理 國防科技大學作者趙雲、張煌有一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智能化戰爭的倫理審視〉對AI武器系統自主作戰的倫理問題有很好的分析。這可以分三個範疇討論: 「開戰正義」:指涉訴諸戰爭的權利和合法性的問題。智能空間(包括網絡路空間)的主權與全球公域邊疆有爭議,而有能力發動智能化戰爭的主體數量大大增加,非國家的組織崛起,技術雄厚的大公司和恐怖組織都可以輕易使用。當技術變得低成本、武器可使戰爭做到接近「零傷亡」和「軟殺傷」,戰爭製造者更少顧忌發動戰爭的成本,從而導致小型戰爭更加容易爆發。AI系統必然含有「先發制人」的設計,一旦計算好後果可以接受便可以開戰。 「交戰正義」又稱戰爭行為正義,上面Scharre和他的團隊面對阿富汗小女孩的決定就是例子。一般而言,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參戰各方必須遵循的倫理規則包括「區別性」原則和「相稱性」原則,避免無區別性的濫殺,以及使用與情境和目標不相稱的毀滅性武力。機器人雖然有人工智能,但卻沒有憐憫或悔恨等情感,殺人不會沒有任何的愧疚感,因此,戰爭的目的可以淪為為屠殺而屠殺。 「終戰正義」:這或者可以更準確地稱為「戰後正義」。清算戰爭罪行、釐清戰爭責任是「戰後正義」的首要體現 (其他方面包括承擔戰後重建的義務問題等) 。相對於傳統戰爭中人類就是唯一的責任主體,在使用自主無人智能武器上面,誰要為違反人道規約的作戰決策負責?這在目前難以定論。責任分配是一大困境:武器操控者、軍火商、設計AI的工程師、選擇武器的採購員、戰地指揮員、相關維修保養人員乃至AI武器本身,一大串相關的人和系統,全都可能有責任,但也就是說,追究責任的難度極大。 這些議題也可以橫向思考:AI系統代替人類自動決策,衍生的倫理問題並不限於武器殺傷摧毀而無法問責。自主系統用於醫療決策、教育(例如大學收生) ,以至管理社會秩序(例如內地以大數據建立「社會信用計分制」),背後都有嚴肅的問題需要思考。
Poverty affects access to regular source of primary care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醫護專業與病人私隱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5.7.2019)

醫護專業與病人私隱 六月充滿動蕩和衝突,在緊張複雜的警民與醫療互動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醫護人員有專業責任為病人保密,保護病人的福利,但是否同時需要與警方合作,甚至在某些情況底下違反為病人保密的原則? 這個問題並不是香港獨有的,也不是一個新問題。本文取材自英國兩篇相關文章,並因應香港的情況加以剪裁和說明。 尊重病人私隱,為病者保密,這是專業責任,比普通機構保護個人資料的最低法律要求更嚴肅,因為醫患關係不止是一般的服務合約關係,更有嚴肅的病人對醫護專業的信託。保密是維護醫生與病人之間信任的核心,如果病人對醫生能為他保密沒有信心,就會隱瞞病情,醫治就失去基礎。自古以來,醫生以希波克拉底誓言為醫德,近代《日內瓦宣言》進行了更新,無論新舊,都把保護病人私隱看得很重。醫務委員會和醫學會的倫理守則亦貫徹《日內瓦宣言》原則。 為病者保密的義務不是絕對的,但任何違反保密期望的決定為都必須視為例外,披露資料要遵循正確的原則。 在徵得病者同意的情況下披露資料當然沒有違反保密要求,前提是病人的同意必須是自願的,而且充分知情,包括知道披露資料的後果。有些情況下,獲取病人同意並不可能,例如在深切治療病房昏迷的病人,醫生可能要從病人利益出發,與家人商討病情作醫治決定,這是默許同意的推定。 依法律要求披露 其次是依法律要求而向他方提供資訊。這通常是警方。這是一個可能會令人困惑的範圍。臨床工作上醫護人員必須注意,警方並沒有要求披露病人資料的自動權力,也沒有要求提供醫療紀錄的自動權利。如屬必須,警方需要取得法院命令。但是,在警方進行調查時,醫護人員不得向警方故意提供不正確或誤導性的資料。 舉例而言,如果病者在交通事故發生被送進深切治療部,而一名警官要求醫護人員抽取血液樣本進行酒精測試以助法醫調查,醫護首先要知道這是否法例要求,因為樣本必須是合法的,否則法院不能使用其化驗結果。這些程序應該由書面提出請求,並經確認其為合理。 較少爭議的例子是防止恐怖主義,英國2006年《恐怖主義法》要求專業人員向警方通報任何可能有助於防止恐怖主義行為的資訊,或協助逮捕或起訴恐怖分子。這與當前香港的情景無關,沒有人認為在示威衝突中受傷(即使是橡膠子彈所傷) ,就等如恐怖分子。 如果在醫療過程當中,病人承認犯了嚴重罪行,醫護人員要不要主動報警?這是有些灰色的地帶,因為何謂嚴重罪行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名單。英國的醫務委員會(GMC) 在其指引中未有對嚴重犯罪作出定義,但引用了國民保健系統(NHS) 的《保密業務守則》中給出的例子,包括謀殺、過失殺人、強姦、綁架和虐待兒童致造成重大傷害。 披露必須慎重 GMC 提醒,醫生必須平衡披露對病者的影響,以及不披露的話可能對公眾造成的危害。涉及槍支或持刀犯罪的罪行,與例如違例泊車的罪行當然是不同的。如果病人透露在計劃犯罪,而這罪行有具體的對象,在美國,醫生有義務去警告可識別的受害者,即使這有違病人保密的原則。在英國,醫生可能需要更多的證據去確定其他人有沒有面臨受傷害的風險。總的說來,只要醫生行為合理,沒有漠視對其他人的風險,並且平衡了對病人的責任和社會的責任,他不太可能因為披露與否的決定而被控告疏忽。 最後一個重要的公共利益範圍是公共衛生,特別在疫症流行的情況。香港和英國一樣,有公共衛生(疾病控制)法例,要求醫生被通過強制呈報特定傳染病或與工業有關的疾病來提供流行病學資訊。2003年SARS是香港的集體記憶,當時醫管局、衛生署必須依靠警方協助追蹤病人與接觸者,進行隔離。那是一個醫護人員與警方互相合作的戰役,與今天雙方處於互相提防甚至對立局面,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境脈絡。社會躁動竟然令一些前線人員沉不住氣。在此時節,更有必要回到穩固的專業倫理原則,慎重應對。 在香港近日的情境,考慮到以上的原則,或者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判斷: 警方有權逮捕被合理懷疑干犯嚴重罪行的人,警方也有權在醫院進行逮捕,但是否適宜在動蕩和大規模衝突的局勢中立即去醫院進行逮捕?這並不是一個原則性的道德或法律問題,而是涉及更複雜的、是否明智(prudent) 的判斷; 醫生和護士並沒有義務協助警方去尋找或識別示威抗議中受傷來求醫的人士,更不應協助作出逮捕,除非有法院命令; 如果有醫院行政人員或前線專業人員主動向警方作通報,讓警方拘捕在示威中受傷的人士,這一定是違反專業的,除非是有明確的資訊,判斷若不通報,這些人士對公眾會有嚴重而具體的危害。 參考: K Blightman, SE Griffiths. Patient confidentiality: when can a breach be justified?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Anaesthesia Critical Care & Pain, Volume 14, Issue 2, April 2014. C Wills. Confidentiality: When can […]
Journal Club: “Being Accountable for Medical Errors: Observations on Hong Kong vs Australia”

Date: 11 July 2019 (Thursday) Time: 5:00 – 6:30 p.m. Venue: Room 239, Sino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Dr Alastair Mah, Senior Manager, Patient Safety & Risk Management, Hospital Authority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Powerpoint Slides by Dr. Alastair MAH – “Being Accountable for Medical Errors: Observations on Ho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