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tial educational patterning of cardiometabolic risks between women and men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Chinese adults in Hong Ko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obesity.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Webinar Series] Seminar on “Genomics for Health – Addressing Ethical and Social Concerns”

Date: 11 May 2021 (Tuesday) Time: 10:30 a.m. – 12:15 p.m. (Hong Kong Time) / 12:30 p.m – 2:15 p.m. (Sydney/Melbourne Time) / 2:30 p.m. – 4:15 p.m. (New Zealand Time) Venue: The seminar will be conducted via Zoom. The meeting ID will be sent to registrants by email. Speakers: 1. Prof. Catherine Mills, Director, Monash Bioethics Centre, Monash University (Topic: “Your Choice: Reproductive […]
Quality of life and its contributors among adults with late-onset Pompe disease in China.
恢復探訪是倫理難題嗎?(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9.04.2021)

上月我為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的內部培訓研討講了一個特別的課題: 「謝絕探訪措施下的倫理反思」。COVID-19 疫情已超過一年,無論是醫院抑或安老院, 基本上都處於一個謝絕探訪的狀態。固然,這些機構都有不同的安排,協助院友和親友保持一點聯絡,也有酌情容許恩恤探訪。不過無可否認的是,住在醫院或院舍的人,都要忍受著疏離甚至隔絕。在其他國家地區,有些醫護人員,尤其是護士,為此感到甚為不安。 這在倫理學術語稱為「道德困擾」(moral distress)。院牧同樣會為探訪難而感到困擾,因為「靈性關顧」(spiritual care)並不是可有可無的。醫管局為此有特定的行政安排,例如讓指定的院牧在嚴格跟隨感染控制指引的條件下,維持必須的服務,包括探訪臨終病人。在這次講座我為大家探討兩個焦點, 一是從倫理角度,我們可以怎樣分析和思考限制探訪的問題;二是如果往前看, 我們怎樣可以合理地計劃在疫情容許之下,逐步恢復探訪安排。 謝絕探訪 患者感孤獨 在討論倫理角度的之前,我們可以注意兩點。第一,這個議題本身並不是一個強烈的道德問題,也就是說,它並不像安樂死、墮胎之類的生命倫理議題,從一開始就有正反對立的道德立場;第二, 醫院或安老院日常需要有探訪規定,也就是一定程度的探訪限制,而在傳染病流行底下,這些限制變得較嚴,一般人都會視為合理。從這兩點看,限制探訪甚至謝絕探訪好像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倫理問題? 我們可以首先明確地列出限制探訪的一些重要理由。醫院和安老院機 構,在照顧病人與長者的時候,首先必須保護他們的安全。限制探訪或謝絕探訪,最大的理由是把院友的感染風險減至最低。盡力減低感染風險,從另一方面看,當然也是在保護機構本身,減低一旦出事機構面對的法律風險。在疫症大流行,保護醫院和院舍機構運作,也是抗疫戰的關鍵。 香港對抗瘟疫,是帶著 2003 年沙士一役病房淪陷的慘痛烙印,因此我們公立醫院的探訪限制一般都比歐美澳洲等地的醫院較緊。在疫情底下尤其如此。從網上的資料,可以見到即使 COVID 疫情嚴重,一些主要醫院在設定探訪限制上,仍然會容許一個探訪者探訪某些指定的專科病房,例如產科病房、兒科、紓緩治療病房等。這在香港多年已經習慣的防感染尺度,是有些難以想像。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要求放寬探訪限制的一些理由。 本文開始時已經提到,限制探訪令院友孤獨,與親友疏離,也阻礙了重要的靈性照顧和情緒支援。不少認真的研究發現, 嚴禁探訪不只會造成普通的寂寞,對於病人、院友,尤其是長者我本身有認知問題的人士,隔絕了和親人的接觸,是會造成實質的身心損害。短期限制或者不是一個問題,但長期如此,損害就較大。去年 12 月日本一個研究團隊發表一份報告,在 6000 多名平均七十多歲的長者病人,已實施探訪限制的前後時期作對比,發現嚴格限制探訪知 下,長者病人出現譫妄症(delirium)的機率是之前的 3.79 倍。譫妄症表現為神智昏亂,在醫院病房,昏亂本身又會引發其他問題,例如需要約束病人, 造成餵食困難,間接再引致其他併發症。 長期實施嚴格的探訪限制,說嚴重一點,可能有人道和道德上的問題。說到底,嚴限探訪以減低風險並不是經過嚴謹研究證明必要,比較是基於合理估計作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措施。於是便有論者提出, 如果我們承認限制探訪的程度,應當是從權衡利弊作合理平衡出發,那麼便可以 問,對於探訪和人倫接觸的重要性,我們是否看得太輕了? 有一個比較強的觀點是,人倫接觸本來就應該是常規醫療照顧的標準要求(standard of care) ,每一次我們決定把這個標準降低或放開,都必須經過認真考慮,是不是機械式地實施限制。 相稱原則和公平原則 以上的正反討論還是屬於常情常理層面的正反分析,未算是嚴謹的倫理討論。 從倫理原則看,有兩個原則是比較相干和重要的。一是合符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或譯作相稱原則) ,這個原則在法律方面常常應用,具體的要求是當自由需要受到限制,所設定的措施應該盡可能採用最低度的限制方法(Least Restrictive Measure);另一個倫理原則關乎公平(Fairness),特別是對不同人群的需要是否有一貫的近乎一致的尺度(Consistency)。人們可以問,為什麼連戲院都可以重開,運動可以恢復,飲食也逐步放寬,但逐步放寬探訪措施卻完全不在討論議程上,我們總不能 說,一個院舍長者或醫院病人與親人見面傾談,得到安慰,他的需要竟然不比飲食聚會、運動和看電影更重要?對於這些倫理角度的質疑,如果必須為現行措施辯護的話,恐怕還是只有從「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顧慮出發, 解釋為何醫院或院舍需要有很高的安全系數,因為實在承受不了,一旦在病房或院舍大爆發,那種難以收拾的局面。 本文定稿時,政府剛公布一系列社交放寬和重啟經濟的分階段安排,安老院舍探訪安排亦獲得放寬,訪客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後,可以到院舍探訪親友。疫情持續逾年,安老院舍的長者長時間無親友探訪,心理和情緒受到很大困擾,現在開始放寬是應有之義,希望公立醫院很快也可以放寬。在限制探訪的問題上,筆者向來的看法是,最少最少,我們不應把探訪限制視為理所當然,更不要習慣了以視像方式看望一下取代親身接觸。 下一步還要以同理心為未曾接種新冠疫苗的家屬訪客,提供合理的探訪安排,盡力減少差別看待。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Webinar Series] Seminar on “AI in Future Healthcare – Considering the Moral Dimension”

Date: 14 April 2021 (Wednesday) Time: 4:00 p.m. – 5:45 p.m. (Hong Kong/Taiwan Time) / 6:00 p.m – 7:45 p.m. (Melbourne Time) / 9:00 a.m. – 10:45 a.m. (UK Time) / 10:00 a.m. – 11:45 a.m. (Germany Time) Venue: The seminar will be conducted via Zoom. The meeting ID will be sent to registrants by email. Speakers: 1. Dr. Sarah Chan, Reader in […]
The Emergence and Global Spread of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Evolution of Bioethics Education in the Medical Programme: A Tale of Two Medical Schools.
長者接種新冠疫苗誰決定?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2.03.2021)

疫苗接種計劃展開了,科興疫苗之後是BioNTech(「復必泰」) ,市民反應不算冷也不算熱,這其實是好現象,留有空間弄清楚一些基本資訊和合理的疑問。10多萬人接種了,有一些打針後不適入院和死亡個案,說不清有沒有超出「背景死亡率」的合理範圍,令人生疑慮,這便有親友來問我意見。問題多是這樣的:「我家老人xx歲,有xx等病,長期複診,平時血壓有時偏高(或偏低),應該給他打科興還是復必泰?」我會開始「問症」,然後謹慎給意見。意見必須謹慎細說,因為答問其實藏了倫理題,關於長者接種由誰決定?基於什麼來下決定? 大原則是清晰的:腦筋清楚的長者應盡量自主地作出決定,決定的基礎是「知情同意」;在有認知困難的長者(法律上的「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即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s,簡稱MIP) ,其他人代做決定時要以長者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為基礎。 一般來說,無論是「知情同意」或「最佳利益」,都需要具體考慮接種和不接種的風險和好處,權衡利弊。考慮讓長者接種哪一款疫苗,原理也相同。 可是,具體地給接種的建議時,這些原則不是很容易恰當地執行的。即使長者腦筋清楚,也不容易獲得平實易明的資訊作決定。長者本身多有長期病患,衛生當局建議先諮詢醫生,這很合理,但是下一道問題是醫生又當如何建議才算盡了專業責任? 衛生防護中心和衛生署合作製作的「接種須知」內容(「克爾來福」即科興疫苗、「復必泰」即BioNTech疫苗,各有單張) 是有用的起點。科興疫苗單張的「注意事項」列得比較具體,例如糖尿病患者或有驚厥、癲癇、腦病或精神疾病史需慎用。BioNTech疫苗單張的「注意事項」較簡略,沒有特別提到糖尿病、癲癇、腦病或精神疾病,但特別警告如有出血問題,容易出現瘀青或正在使用預防血凝塊的藥物,應先諮詢醫生、藥劑師或護士。 醫生建議應深思熟慮 網上和流傳一份內地的「新冠疫苗重點人群接種22問」,內容比香港具體和細致,例如痛風發作期不宜接種疫苗(因為 所有嚴重急性疾病和慢性病的急性發作期都不宜接種) ,又例如具體說到,未受控制的高血壓(界定為收縮壓≥140mmHg,舒張壓≥90 mmHg) ,不得接種新冠疫苗。這令香港衛生當局也有壓力,要提供更多細節的「不宜接種」的接指引。 中國內地的「接種22問」是發佈於今年1月初,當時內地的接種計劃還在開展初期,界定接種的條件傾向保守,例如不為60歲以上的長者接種,到最近第二階段才讓健康的長者逐步加入。本來,讓長者優先接種是國際共識,但內地反其道而行,這是不是因為對疫苗的安全性仍有戒心?我看其中可能含有推廣策略,因為若讓長者先接種,必會因「背景死亡率」造成群眾疑懼,而一旦疑懼成形,接種率就很難快速提高。香港目前的情況就可是這樣。內地讓長者遲一批才打針,或者也有「生產力優先」的價值觀在主導?我們不宜妄斷。無論如何,我認為香港是難以完全照搬內地的一套。 在「知情同意」上面,醫生給意見應是經過深思熟慮,不宜粗枝大葉地叫人「打得就打」。推廣接種是一回事,醫患關係中盡責是另一回事。醫生(闊一些是醫學界) 的基本責任是努力消化各個來源的數據、指引資訊,謹慎但正面地給意見。協助病人做決定時,要評估病史和病情,要尊重病人的意願和具體需要。當然也可以顧及多些人接種對保護群體的好處間接也是保護面前的這個病人,但主次是有別的。 來到為「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MIP) 決定接種與否,更是需要審慎。院舍長者中,因嚴重中風和患腦退化症的MIP不少,若有指定的法定監護人(legal guardian) ,而醫生認為適合,可以監護人簽署同意書給MIP長者接種;在大多數情況,MIP長者並沒有正式監護人。社署給院舍的指引是,長者如屬MIP又沒有法定監護人,院舍要諮詢院友的家屬(如有)的意見。如果家屬不同意接種,則需收集家屬不同意的原因,供外展醫生參考,再評估及根據院友的最佳利益決定院友是否適合接種。筆者聞說有些家屬甚至院舍員工對此有些疑惑:是否即使家屬反對接種,醫生仍會單方面決定給MIP院友注射疫苗? MIP決策權存灰色地帶 這裡面有一個醫學倫理問題,即醫生應如何與 MIP 的家屬分享醫療決策權。在香港,法律上容許醫生為沒有監護人的MIP長者作迫切的重要醫療決定,但在接種疫苗,特別是新面世的疫苗,可能是有些灰色地帶。接種疫苗有益亦有風險,在香港的疫情底下,醫生如何判斷必需接種?無論從倫理學角度或在臨床實踐,醫學界也不大贊成把「病人的最佳利益」狹窄地理解為純技術性的醫學決定。醫生掌握醫學知識,但家人往往更瞭解長者的性情喜惡,所以需要有共同的決策過程(shared decision-making) ,為長者尋找合適的方案。 以上談論院舍的情況,可能還是有些「離地」。院舍長者多病,醫生的角色實際上只可以為他們評估,篩選剔出不宜接種的長者,而未必適宜單方面像處方那樣指示不能自決的MIP長者接種疫苗。「適合接種」、「應該接種」和「必須接種」是不同層次的判斷。保持正面態度與家屬及監護人商討,審慎地共同決策是重要的。
新冠疫苗的知情同意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2.02.2021)

香港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刻下正在啟動,在這臨門階段不適宜作過於複雜和理論性的倫理分析,當務之急是做好「知情同意」程序的準備。我相信衛生署、專家顧問、醫學組織的同行都在努力,或者連疫苗的資訊單都早已就緒。本文嘗試綜合講解有關接種新冠疫苗的「知情同意」的三個方面:一、誰應該(或不宜)接種;二、不良反應包括過敏反應的風險;三、選擇哪一款疫苗? 誰應該(或不宜)接種?在我讀到的建議指引,較完整的是世衛在1月8日發佈的暫行指引(Interim guidance) 。讀者可以從Google 以「WHO interim recommendation BioNTech」字串搜尋找到全文。 世衛指引具權威性,但聲明「暫行」,這是平實的做法,因為資訊和數據時常在更新中。這指引的主角是率先被世衛認可的「BioNTech/輝瑞/復星」RNA疫苗(下稱「BioNTech疫苗」) 。按指引,絕對不宜接種BioNTech疫苗的情況寥寥可數。這包括過往曾在接種其他疫苗產生嚴重的敏感反應,如急性的過敏反應(anaphylaxis) 。嚴重的過敏反應有些其實不是對疫苗本身敏感,而是個別疫苗針藥含添加劑聚乙二醇(PEG),因此對PEG有嚴重過敏反應史的人士也不能接種。 世衛指引接著細致講述對各類群體的建議和建議的基礎,並如實說明一些建議在現有科學數據上的不確定性。基於缺乏足夠數據,暫時不建議接種的群體包括孕婦和16歲以下的兒童。 知情同意的第二方面是提供不良反應和過敏反應風險的詳細資訊。要注意的是,有關不良反應的風險資訊,不宜為了預防法律責任而硬繃繃地羅列,就當是已經讓人「知情」。早前國內有一宗小風波,一個上海疫苗專家在微博上傳了國藥疫苗的說明書電子版,說明書上面列出林林總總的臨床試驗不良反應,有73種之多。這個專家笑說這疫苗「一舉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文章迅速被刪除,他須再次發文道歉,並承諾會以身作則接種國藥疫苗。他的取笑行文失諸輕佻,但這其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題目:臨床試驗規定要報告所有發生不良反應的事件(adverse event) ,但不良反應屬於原始數據(raw data),並不就是臨床需關注的藥物副作用。 BioNTech疫苗在推出使用後,迅即有系統地分析了大量人口接種後的風險數據。這是在2020年12月14日至23日,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對189萬多名接受首次接種後的監測,包括發現21例在注射後的過敏症病例(即每百萬劑11.1例),其中71%發生在接種疫苗後15分鐘內。過敏反應可以用抗敏感藥物和腎上腺素即時處理。 在國內已接受國藥疫苗注射的人口應有2千萬,當局亦設有系統監測不良事件,如果能作系統分析和公布發現,會有助後來接種者的知情同意。這個方向的確是比硬繃繃地臚列一切臨床試驗不良反應更好,因為有關不良反應和過敏反應風險的資訊應該以病人為本。 知情同意的第三方面是選擇哪一款疫苗。本文付梓前,政府剛宣布科興疫苗獲批作緊急使用,100萬劑趕快抵港,成為最先可以接種的新冠疫苗。雖然科興疫苗先至,但很快BioNTech疫苗也會到來(相信3月可以使用),下半年還有第3款(英國疫苗) 會到港 ,市民是可以選擇稍等一下才接種的,這就有了如何選擇疫苗的問題。完整的知情同意必須提供恰當的醫學意見,講解利弊協助病者(在疫苗計劃則是接種者) 選擇。 因為有「國產」/「洋貨」的感情和政治因素,清晰的講解也多了一重避忌,專家和衛生當局也是有些含糊,訊息好像是說,所有獲批作緊急使用的疫苗都是及格的,因此也是差不多的,選擇哪一款疫苗只是看個人喜好。筆者認為,知情同意不宜摻雜對「國產」與否的正負情緒,一切應基於資料的客觀性、完整性和確定性。知情同意也不屬個人喜好的範疇,市民可以問,醫學團體和衛生當局有責任盡量清晰和完整地講解。 早前我在他報專欄寫過一段分析,提醒要恰當地比較各款疫苗的「效能」(efficacy) ,當中是這牽涉到一些看來簡單但並非自明的概念,可以在這兒也講解一次。 假設3款疫苗的保護效能如下:經第三期臨床試驗,A疫苗的效能是9成,B疫苗的效能是7成半,C疫苗的效能是5成,乍看相差不大,最多(A與C) 也只差4成,其實不能這樣理解。讓我們假設不接種疫苗的人口在未來一年間會有2%的「中招」發病風險,倘若接種C疫苗,把風險減半,即是還有1%機會得病;如果接種B疫苗把風險減去4分之3,就還有0.5%的風險得病;接種A疫苗把風險減去9成,即尚有0.2%機會得病。選擇A與C最終的風險差別是0.2% 與 1% 之比,不是表面看的相差4成,而是相差4倍! 倘若差別是這樣大,A疫苗豈不是必然的首選?然而「效能」並非選擇疫苗的唯一考慮,一般相信,傳統方法研製的「滅活疫苗」(例如科興疫苗、國藥疫苗)的副作用比科技研發的「RNA疫苗」(例如BioNTech疫苗、香港沒訂購的美國Moderna 疫苗) 會是較少或較輕,原則上每個人可以按自己的「風險胃納」和對高效能的要求作選擇。不易確定的是,兩類疫苗的安全性差別有多少?專家應可提供分析。 另外,筆者也認為,政府宜留意國藥疫苗。國藥未有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數據,如果數據證明效能一如宣稱有79%,則棄科興而轉為訂購國藥疫苗也是負責任的做法,因為選用高效能疫苗會有助建立全民的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 。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Programme 20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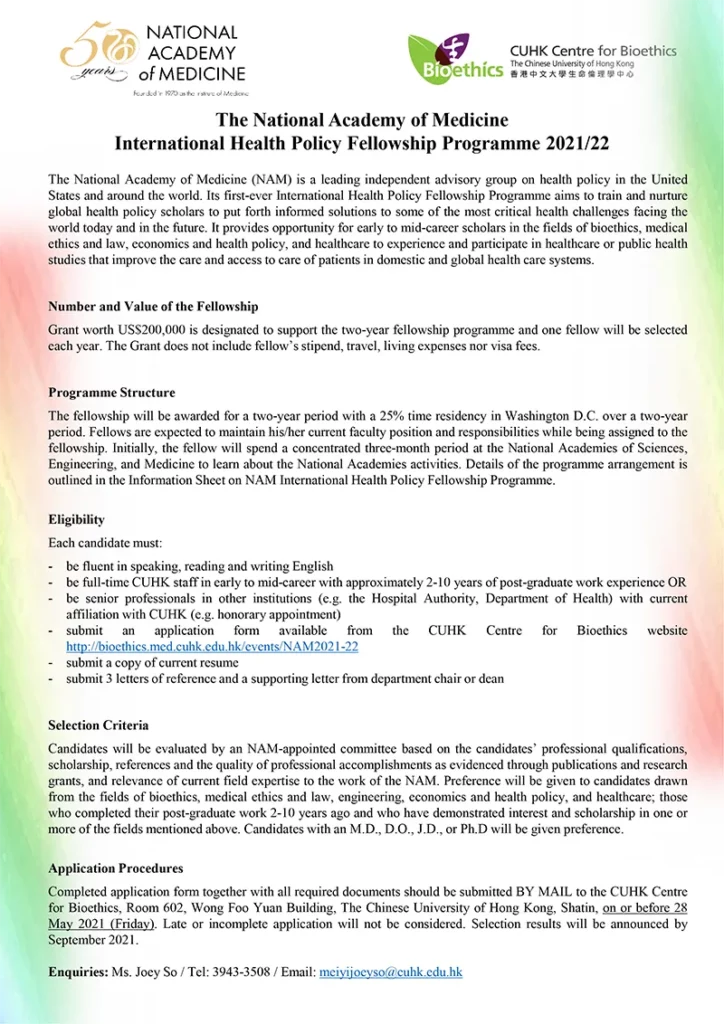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NAM) is a leading independent advisory group on healt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Established in 2017, its first-ever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Programme aims to train and nurture global health policy scholars to put forth informed solutions to some of the most critical health challeng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