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inar 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OVID-19: Ethics, Equity and Public Heal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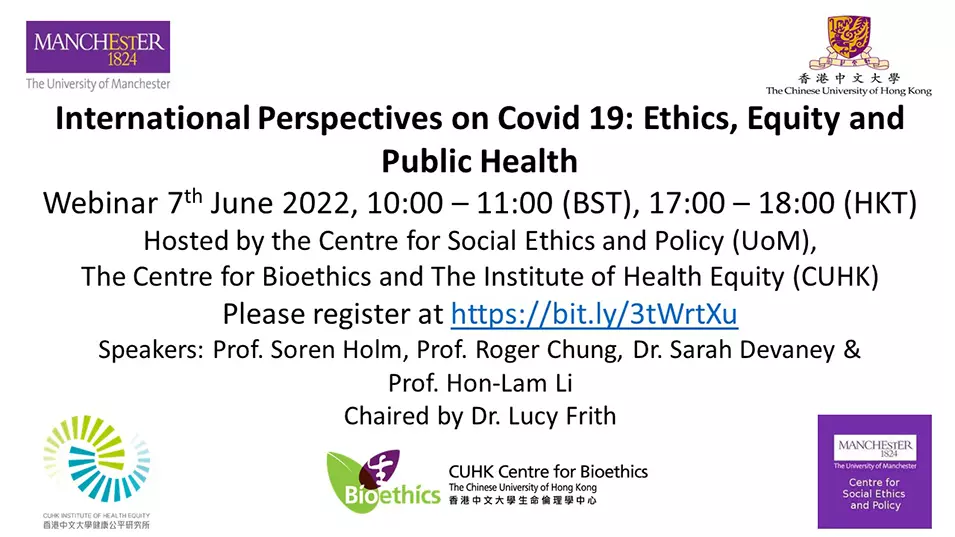
Date: 7 June 2022 (Tuesday) Time: 10:00 a.m. – 11:00 a.m. (BST) / 5:00 p.m. – 6:00 p.m. (HKT) Venue: Online via Zoom Webinar Speakers: 1. Prof. Søren Holm, Professor of Bioethics, Centre for Social Ethics and Policy, School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Topic: “Understanding the Early English COVID-19 Response – Uncertainty, Epidemiological Factors, and (a lack of) Policy Options”) 2. […]
等待「預設醫療指示」立法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30.05.2022)

政府行將換屆,自必有各種新的政策構想,但是有一項立法工作已經接近提上立法會的階段,現屆政府做了很多準備,筆者企盼它在不太久的日子後能夠實現。這是在香港為「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簡稱AD)立法,去年本欄曾簡介政府的立法建議。(〈立法有助預設醫療指示〉,2021年9月13日。)本文承接了那篇文章一些焦點,退一步講述基本的概念,也談談是項立法對病人和醫護人員的重要性。為什麼需要退一步講?是因為預設醫療指示立法的背後有重要的倫理學原則,在香港的實踐也有具體的背景脈絡。清晰的概念應會有助穩步向前走。 第一個概念應該引用香港醫務委員會專業守則(「守則」)第34節有關「對末期病人的護理」的條文,其中明確表明,「當病人危殆時,醫生的責任是小心照顧病人,盡可能令病人在少受痛苦的情況下有尊嚴地去世。醫生要尊重病人對控制其症狀措施的自主權…」(34.1段),而「停止給垂死病人提供依靠機械的維持生命程序或撤去有關程序並非安樂死。」(34.3段) 不可與安樂死混為一談,是至為重要的概念。不少病人在生命末期不想不由自主地依靠各種維持生命程序延長日子,自主拒絕某些維持生命的治療,是受法律保障的權利。「守則」2.1段列明,「在法律上,醫生不得向不同意接受治療的病人施行診斷程序及醫治。醫生這樣做可被起訴侵權(如毆打),或被控如傷人及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等刑事罪行。」 預早決定應得尊重 第二個概念是,病人可以預早作出決定,日後在特定情況底下拒絕接受某些維持生命的治療,無論在法律或倫理學角度,預早指示和當場拒絕治療應該同樣得到尊重。 尊重預早作出決定當然也就是AD的核心要求。據政府於2019年的公眾諮詢文件,透過AD,「作出指示的人在自己精神上有能力作出決定時,指明自己一旦無能力作決定時所拒絕的治療。」在目前醫管局的應用上,指示通常由患有嚴重、不可逆轉的疾病的病人透過預設照顧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訂立。(《晚期照顧: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2.1段。) 為什麼要預早作出指示?因為在病情末期,以及不可逆轉的昏迷、植物人狀態等情況,病人已經無能力作醫療決定,遑論當場拒絕治療。因此,他們可能會被動地施予諸如心肺復甦術(CPR) 、插喉(intubation) 、駁上人工呼吸機、鼻胃管(胃喉)餵飼等維生措施。根據個人意願在精神上有能力作出決定時預早指示,是很有用的。 第三個概念是,雖然目前病人依據普通法也可以訂立AD,但是以條例具體立法仍然是很有必要的。這可以分兩方面看。從病人立場,既然經過深思熟慮訂立了AD,當然期望在需要執行時,有明確的法例規定醫護人員以至家人,完全遵照自己預早作出的對拒絕維生措施的具體指示。從醫護人員角度,立法有助他們實踐良好的專業倫理原則,即是尊重病人自主以及減少痛苦。 第四個概念是,當病人已訂立有效(valid) 的AD,而病況已來到適用(applicable)的情況,醫生不可以單方面以病人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為理由推翻病人預設的指示。這樣的矛盾在現實的臨床情景是有可能出現的,因為病人對於拒絕維生措施的抉擇,常是含有個人對生死以至醫治的價值觀,而醫生考量病人的最佳利益時,往往從醫學角度出發,儘管近年醫學倫理對何謂「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也有較寬的理解,即是說,病人的價值觀能得到尊重,也是廣義的最佳利益。 疏理矛盾方便依循 在目前普通法框架的AD使用情況,有些現有的條例是有可能造成不確定性甚至法律障礙。例如根據《精神健康條例》,面對無行為能力的病人,醫生是可以作出醫學判斷,根據最佳利益原則施以治療的。當然,在一般情況下,醫生並不會單方面推翻病人預設的指示,但是不確定性是存在的。政府的AD立法建議包括會在《精神健康條例》作出具體規定,使有效且適用的AD具凌駕性,筆者認為十分可取。 同樣地,立法建議也會改變現行《消防條例》有關救護員必須復甦患者的責任規定,讓救護員在執行上可以接受和按照AD對不作CPR 指示,免除病人被動地被施行違反意願的急救。 以上解說的出發點,是基本上贊成早日為AD立法,令實踐上能有所依循。那麼AD立法是否有百利而無一弊?不是說「一法立,一弊生」嗎?普通法常以判例來形成準則,若有灰色地帶,可以把新的爭議提上法庭再論,條例立法較清晰但各種規定是比較硬性,因此對於本身對AD立法有疑慮的醫護人員,可能首先會問,立了法例,會否很容易跌入法網?會否有各種刑事責任隨之而來。 在諮詢階段,筆者理解AD立法的用意,是把普通法底下應用AD的原則明確化,而非新增更為嚴苛的規管。當局亦一貫地期望立法可以有助推行AD在香港的使用,所以會有修訂《精神健康條例》和《消防條例》的相關條文的建議。基於這兩點理解,筆者對今次立法有樂見其成的心情。 在這個有點複雜性和已經有些歷史的議題,維持清晰的概念和原則十分重要。讀者如果想重溫AD立法建議的來由,可以網上取閱2020年7月政府發表的諮詢報告《晚期照顧: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 (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consultation/190900_eolcare/c_EOL_consultation_report.pdf) Click here to download PDF Click here to download image
The 16th Symposium on “Bioethics from Chinese Philosophical/Religious Perspectives” (organized b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ate: 28 May 2022 (Saturday) Time: 9:30 a.m. – 12:05 p.m. ; 2:00 p.m. – 4:40 p.m. Venue: Online via Zoom Language: Putonghua Zoom Meeting Details: -Meeting Link: https://hkbu.zoom.us/j/91347271962?pwd=NHNSNmFiS3lWT0lWRU9HMzQwR0FLdz09-Meeting ID: 913 4727 1962 (Password: 497150) Poster: Please click here
The 4th Asia Pacific Bioethics Education Network (APBEN) (co-hosted by CUHK and AMSA Monash Malay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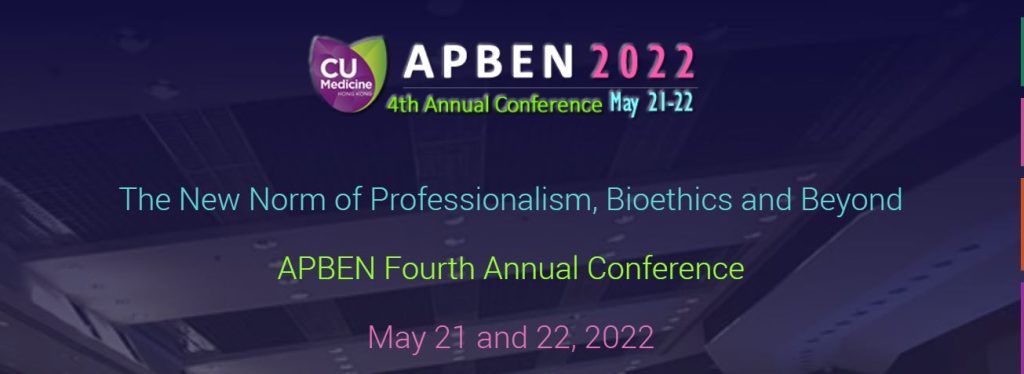
Date: 21 – 22 May 2022 (Saturday – Sunday) Time: 9:00 a.m. – 5:10 p.m. (HKT) (Day 1); 9:00 a.m. – 4:45 p.m. (HKT) (Day 2) Venue: Online via Zoom Programme Details: https://webapps.med.cuhk.edu.hk/apbpmed/APBP/mtg2022/index.html To re-visit the abstracts and video presentations, please click here (see “Oral/Poster Video Recordings”).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 of APBEN (here) for […]
「塗黑臉」扮菲律賓家庭傭工:種族定型與平等機會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2.05.2022)

最近無線電視TVB《金宵大廈2》因為演員黃婉華在第4個單元《姐姐》劇中飾演菲律賓外傭時把自己的面「塗黑」(Brownface),引來關注與爭議。討論源自於法新社港澳台分社主任泰勒4月13日的一則推特,推文中質疑為何在這個世代香港傳媒還會有「塗黑臉」來飾演其他人種的安排。TVB隨後在4月14日發表道歉聲明,強調絕無意在任何節目中表達不尊重或歧視任何國籍,並向可能受此事影響之人士表達歉意。該劇隨即下架,經刪剪再播放。4月20日,黃婉華亦向受此事影響人士表示歉意。這事件並不入於生命倫理學的傳統範圍,但生命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對社會平等的關注和判斷是非的方法,或者亦可提供有用的視點。 事件在國際輿論發酵外,也引來在港菲律賓人士的強烈不滿。批評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將臉及身體塗上棕色這種Brownface行為是有用來譏嘲有色人種的歷史背景,所以本身已經涉及種族歧視;(二)這個角色進一步延續港人對於外傭的刻板印象;而(三)電視劇可以聘請合法的菲律賓人來演這個角色。 第一類批評針對的是「塗黑臉」這個帶有種族主義的行為。「塗黑臉」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早期的美國。當時美國還是奉行奴隸制度,黑臉扮裝表演(Minstrel shows)以白人化妝飾演黑人,並以歌舞滑稽演出來取笑黑人為主題,為觀眾帶來娛樂。這些黑臉扮裝表演在當時大行其道,更在十九世紀中期加州掘金熱時期延伸至塗上較淺的棕色以嘲諷華人,並與1882年的「美國排華法案」產生保存美國民族純正度的相互效應。1927年歷史上的第一齣有聲電影The Jazz Singer亦以一位黑臉扮裝歌手來作為故事的骨幹,可見其普遍性及受歡迎程度。但筆者必須指出,皆因香港並不像美國有那麼根深蒂固的「塗黑臉」歷史背景,這個批評較難直接應用於香港的處境當中。筆者認為第二及第三類的批評更能觸碰到問題的徵結。 刻板誇張 第二類批評針對的是種族定型。在「塗黑臉」的表演,演員除了把自己的膚色塗深外,常會把與那些種族有關的一些行為舉止及說話口音刻板地誇張化。在美國,經過六十年代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社會普遍對「塗黑臉」扮黑人的容忍度大減,但反而助長了「塗黑臉」扮其他有色人種(尤其是拉丁裔及亞裔)的風氣。1961年Mickey Rooney在《珠光寶氣》( Breakfast at Tiffany’s)中扮演大聲(喜歡從樓上大喊到樓下)、野蠻(甚至會用武士劍來嚇人)、市儈(每次開口都是追討租金)的日本包租公就是那個年代的種族定型經典例子。在今次的事件當中,不少在港菲律賓人認為,黃婉華飾演的菲律賓外傭角色也像舊荷里活電影中的少數族裔那樣,被描繪得非常刻板,固化了深膚色與愚昧落後之間的聯想。 出身於菲律賓與華人結合的家庭,同為演員的文翠湄指這角色被編寫得既「愚笨」又「順從」,而香港國際移民聯盟主席埃尼(Eni Lestari)也認為該角色不但刻板甚至古怪,例如會有使用菲律賓巫術、結局最終變回「中國人」等的奇異設定。 種族定型除了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外,它亦與被定型群組的健康(尤其是精神健康)有關係。社會學家David R. Williams與心理學家 Ruth Williams-Morris早於2000年便綜述了在學術文獻中對種族主義和健康之間的關係的研究結果,發現種族定型確實能透過負面的自我評價損害有色人種的精神健康。 制度問題 而第三類批評針對的是聘請演員時的不平等機會。文翠湄認為:「香港的菲律賓人社區很大, 我們是香港最大的少數族裔之一, 電視劇本可以聘請合法的菲律賓人…」這個論點所主張的是在情況許可下,應該找一些更能準確地飾演該種族的演員來擔當角色。 事實上,在近二十年左右,荷里活電影及電視劇中以白人演員來化妝飾演有色人種的風氣已漸式微。例如,史提芬史匹堡上年重拍著名歌舞片West Side Story時都找來拉丁裔的演員來出演拉丁裔的角色,而Natalie Wood在1961年的原版(《夢斷城西》)則塗深膚色來出演那個角色。但對於聘用少數族裔飾演其種族的角色,有些聲音仍然是不以為然的;例如,TVB總經理曾志偉早前曾這樣說:「咁如果拍戲講外星人,我哋搵人扮外星人又係歧視咩?完全係根據劇情需要。」我們當然不可能找到外星人來演外星人,但香港的確有很多菲律賓人——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的估計,菲律賓人佔全港人口約2.5%。 居港的菲律賓人不少,但文翠湄對於菲律賓人角色應由菲律賓人扮演的主張是否很容易成立呢?這涉及一個較深層次的現實,就是大部份在港的菲律賓人都是限於做外傭工作才被准許居留。換言之,要在香港實踐像美國那樣聘請同種族的少數族裔演員(還要是合適的演員),其實是困難重重的。歸根究底,香港並不容許外傭歸化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所以,今次事件所揭示的不僅僅是個別演員或創作團隊的問題,更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制度問題。要解決少數族裔在港得不到平等機會的問題,除了提升對這些種族議題的意識和敏感度之外,我們還得反思制度上的難題。
Resili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older adults in Hong Kong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a mixed methods study.
開展生命倫理教學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4.04.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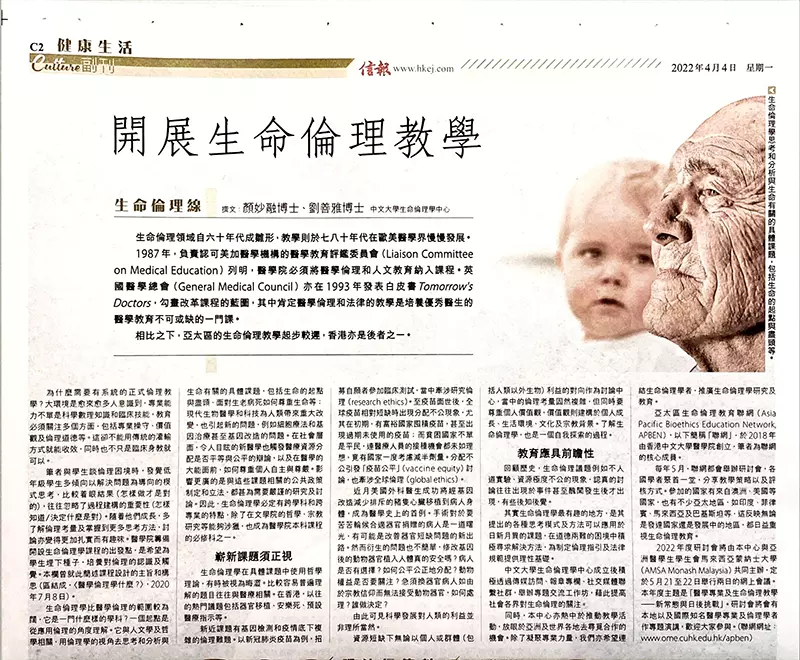
生命倫理領域自六十年代成雛形,教學則於七、八十年代在歐美醫學界慢慢發展。1987年,負責認可美加醫學機構的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列明,醫學院必須將醫學倫理和人文教育納入課程。英國總醫務委員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亦在1993年發表白皮書Tomorrow’s Doctor,勾劃改革課程的藍圖,其中肯定醫學倫理和法律的教學是培養優秀醫生的醫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門課。相比之下,亞太區的生命倫理教學起步較遲,香港亦是後者之一。 為什麼需要有系統的正式的倫理教學?大環境是愈來愈多人意識到,專業能力不單是科學數理知識和臨床技能,教育必須關注多個方面,包括專業操守、價值觀、及倫理道德等。這卻不能用傳統的灌輸方式就能收效,也不止是臨床身教就可以。 筆者與學生談倫理困境時,發覺低年級學生多傾向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模式思考,比較著眼結果(怎樣做才是對的),往往忽略了過程建構的重要性(怎樣知道/決定什麼是對)。隨著他們成長,多了解倫理考量及掌握到更多思考方法,討論亦變得更加扎實而有趣味。醫學院籌備開設生命倫理學課程的出發點,是希望為學生埋下種子,培養對倫理的認識及觸覺。本欄曾就此簡述課程設計的主旨和構思(區結成,〈醫學倫理學什麼?〉,2020年7月8日)。 概觀生命倫理學 生命倫理學比醫學倫理的範圍較為闊,它是一門什麼樣學科?一個起點是從應用倫理的角度理解。它與人文學及哲學相關,用倫理的學的視角去思考和分析與生命有關的具體課題,包括生命的起點與盡頭、面對生老病死如何尊重生命等;現代生物醫學和科技為人類帶來重大改變,也引起新的問題,例如細胞療法和基因治療甚至基因改造的問題。在社會層面,令人目眩的新醫學也觸發醫療資源分配是否平等與公平的辯論,以及在醫學的大能面前,如何尊重個人自主與尊嚴。影響更廣的是與這些課題相關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立法,都甚為需要嚴謹的研究及討論。因此,生命倫理學必定有跨學科和跨專業的特點,除了在文學院的哲學、宗教研究等能夠涉獵,也成為醫學院本科課程的必修科之一。 嶄新課題須正視 生命倫理學在具體課題中使用哲學理論,有時被視為晦澀。比較容易普遍理解的題目往往與醫療相關。在香港,以往的熱門議題包括器官移植、安樂死、預設醫療指示等。新近課題有基因檢測和疫情底下複雜的倫理難題。以新冠肺炎疫苗為例,招募自願者參加臨床測試,當中牽涉研究倫理(research ethics)。至疫苗面世後,全球疫苗相對短缺時出現分配不公現象,尤其在初期,有富裕國家囤積疫苗,甚至岀現過期未使用的疫苗;而貧困國家不單是平民,連醫療人員的接種機會都未如理想,竟有國家一度考慮減半劑量。分配不公引發「疫苗公平」(vaccine equity)討論,也牽涉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 近月美國外科醫生成功將經基因改造減少排斥的豬隻心臟移植到病人身體,成為醫學史上的首例。手術對於要苦苦輪候合適器官捐贈的病人是一道曙光,有可能是改善器官短缺問題的新出路。然而衍生的問題也不簡單,修改基因後的動物器官植入人體真的安全嗎?病人是否有選擇?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動物權益是否要關注?急需換器官病人如由於宗教信仰而無法接受動物器官,如何處理?誰做決定? 由此可見科學發展對人類的利益並非理所當然。資源短缺下無論以個人或群體(包括人類以外生物)利益的對向作為討論中心,當中的倫理考量固然複雜,但同時要尊重個人價值觀,價值觀則建構於個人成長、生活環境、文化及宗教背景。了解生命倫理學,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 教學應具前瞻性 回顧歷史,生命倫理議題例如不人道實驗、資源極度不公的現象,認真的討論往往出現於事件甚至醜聞發生後才出現,有些後知後覺。其實生命倫理學最有趣的地方,是其提出的各種思考模式及方法,可以應用於日新月異的課題,在道德兩難的困境中積極尋求解決方法,為制定倫理指引及法律規範提供理性基礎。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成立後積極透過傳媒訪問、報章專欄、社交媒體聯繫社群,舉辦專題交流工作坊,藉此提高社會各界對生命倫理的關注。同時,本中心亦熱衷於推動教學活動,放眼於亞洲及世界各地尋覓合作機會。除凝聚專業力量,我們亦希望連結生命倫理學者,推廣生命倫理學研究及教育。 亞太區生命倫理教育聯網(Asia Pacific Bioethics Education Network,APBEN),以下簡稱「聯網」,於2018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創立,筆者為聯網的核心成員。每年5月,聯網都會舉辦研討會,各國學者聚首一堂,分享教學策略以及評核方式。參加的國家有來自澳洲、美國等國家,也有不少亞太地區,如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巴基斯坦等,這反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的地區,都日益重視生命倫理教育。2022年度研討會將由本中心與亞洲醫學生學生會馬來西亞蒙纳士大學(AMSA Monash Malaysia)共同主辨,訂於5月21至22日舉行兩日的網上會議。本年度主題是「醫學專業及生命倫理教學 — 新常態與日後挑戰」。研討會將會有本地以及國際知名醫學專業及倫理學者作專題演講,歡迎大家參與。(聯網網址: www.ome.cuhk.edu.hk/apben)
Explaining the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COVID-19 Among Older Hong Kong Chinese People-A Qualitative Analysis.
預設醫療指示在中國内地的發展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7.03.2022)

Advance Directive (簡稱AD)在香港通譯為「預設醫療指示」,在中國内地稱爲「預立醫療指示」。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劇、醫療水平的進步、以及人們對生命價值的追求,提倡「自主決策」、「尊嚴死亡」的呼聲不斷增强。對AD的推動最先來自民間和醫學界。2006年。一位名為羅點點的女士創立了「選擇與尊嚴」網站,其宗旨是提倡尊嚴死亡,呼籲醫療自主決策權,推廣AD在中國内地的實施。筆者的博士論文以内地預設醫療指示的發展和困難為主題,本文就其中的觀察略為介紹。 2011年6月,「選擇與尊嚴」網站推出首個AD的民間版本,以「我的五個願望」為中心,即:1)我要或不要什麽醫療服務;2)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Life-sustaining Treatment);3)我希望別人怎樣對待我;4)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麽;5)我希望誰幫助我,讓公民通過自願填寫AD來明確表達重要的醫療意見和選擇。「五個願望」涵蓋範圍比AD闊,後三項是非醫療性的預囑。2012年,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臨床腫瘤醫院顧晉主任呼籲,社會各界應重視和認可AD的必要性。2013年,全國政協委員凌峰也提出應將AD納入醫療改革的内容中。同年,首個由民間發起的「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於北京正式成立,通過公衆宣講、系列課程、論壇,及志願者等形式推廣理念,推動AD的實施。 對AD的認知 協會分別於2006年、2012年和2015年做過三次有關中國内地居民對AD的認知度調查。結果顯示居民認知度和填寫意願都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2021年4月,廣東省深圳市成爲繼北京之後,全國第二個成立「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的城市。然而,由於中國內地AD的發展尚未成熟,大部分實踐活動僅停留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 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於2019年初訪談了來自深圳市某重點公立醫院(又稱三甲醫院)的35位受訪者,其中包括12位癌症中晚期患者,12位患者家屬,11位腫瘤科及ICU醫生和護士。訪談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對AD概念的了解程度、對AD的需求和態度、醫療決策的形式和遇到的問題等。約86%的受訪者表示從未曾聽過AD,但對於「尊嚴死」、「自主決策」、「過度醫療」和「舒緩醫療」(Palliative Care,港譯「紓緩治療」)都有一定的了解。有患者表示曾與親屬表達過自己不接受插管和心肺復甦的意願。他們在訪談中多次提到:「體面尊嚴地離去比任何搶救和醫療花費都要重要。」對於患者來說,失去體面尊嚴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藥物都無法控制的疼痛感,第二是全身插滿各種管子,第三是極低的生活質量。多數受訪家屬表示,接受親人離世是痛苦的,但是看到他們在病痛中煎熬卻無能為力則會感到更加痛苦。 在簽署AD的意願方面,所有受訪者都表達如果中國內地能將AD合法化,他們願意提前簽署這份醫療文件,以保障自己日後的醫療決策和權利不受他人侵犯。筆者也發現,有宗教信仰(如基督教和佛教)的受訪者對AD的態度更加開放和包容。 文化影響深遠 在被問及醫療決策的形式和遇到的問題時,大部分受訪者表達了自我決策的重要性,但同時也表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遠影響下,要做到真正的自我決策非常困難。一位腫瘤科醫生在訪談中談及:「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下,很少有家屬會主動和患者討論醫療護理決策。對於病情和診斷,我們通常是先告知家屬。但是否告知病人,何時告知,及告知多少都交由家屬決定。」另一位ICU醫生也表達:「進入ICU的病人基本都處於無意識或昏迷狀態,是否插管或進行心肺復甦我們都是聽家屬的。就算病人曾跟我們或家屬表達過不想插管的意願,最終我們還是會按照家屬的意思來做。畢竟,我們也需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以免家屬事後找麻煩。」 在訪談中筆者還發現,所有的受訪患者和家屬都會將AD與安樂死混為一談。訪談中最常出現的問題之一就是:AD合法化是不是代表我可以進行安樂死了?他們認為安樂死和生命支持治療一樣都屬於AD內容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內地社會對AD的認知度普遍較低,AD的普及教育仍然任重而道遠。 除了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支持,生死觀、家庭倫理、道德觀等因素也成為在中國內地推廣AD的重要障礙之一。中國文化受到傳統儒家倫理的深刻影響,在醫療決策家庭被賦予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傳統的家庭觀認為患者與家屬應視為整體,家庭有權利參與醫療決策,並為病人做出最好的選擇。因此,在醫療決策上,一方面患者依賴家屬作決定,另一方面,家屬藉由對患者的保護往往選擇隱瞞部份甚至全部病情,從而代理患者進行決策。醫護人員為了避免糾紛,通常也將知情權和決定權交給家屬。然而,尤其對於腫瘤患者來說,知情、決策和同意是不可少的。患者能夠積極參與,才能正確判斷病情的發展和預後,把握生存的機會,增加求醫信心和配合治療。相反,家屬的過度參與和保護會加重患者對疾病的憂慮和猜疑,進而產生對醫生的不信任和對生命的絕望。 另外,在儒家思想中,生與死都被賦予道德意義,沒有為生命努力抗爭就放棄生命的人在道德上是「失敗」的。因此,忍耐和不惜一切代價的觀念影響了許多患者和家屬對於臨終醫療的決策。再者,家屬作為代理決策者時往往會受到「孝道」的影響,以為不救治或撤除治療就是「不孝」。對孝道的誤解徒增患者的痛苦,也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浪費。 患者作為決策主體是否擁有完全自主權?家屬是否享有決定權?應如何參與?當患者與家屬對決策產生矛盾,患者受到來自家庭的壓力甚或威脅時,如何平衡其關係?目前中國尚沒有法律承認AD的合法性,也沒有專門的政策條例來規範其實行。日後倘若在中國內地推行立法,就必須正面討論這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