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cept and Conceptions of Personhood: The Fallacy of Jennifer Blumenthal-Barby’s Argument
Employment conditions and mental health of overseas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 parallel mediation analysis
韓國醫生抗爭的倫理疑惑 區結成醫生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2.04.2024)

區結成醫生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榮譽顧問 韓國醫生抗爭的倫理疑惑 韓國住院醫生從2月開始以辭職罷工作激烈抗爭,總統尹錫悅曾堅持不退讓、不談判。 本文截稿前,韓國「全國醫科大學教授緊急對策委員會」宣布支持,16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們由3月25日開始提交辭呈,希望促使政府與醫生對話,調整大幅擴充醫學院招生名額的政令。這是一個不能善罷、病人受害的局面。 抗爭起因是2月6日韓國保健福祉部逕自公布《醫學院入學名額擴大方案》,宣布從2025年3月的新學年開始,國內40所大學醫學院招生上限也將從現行的每年3058人增至5058人,為期5年,即共計增加1萬名醫生。這觸發醫院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強烈反彈,集體辭職罷工,以為可以迫使政府收回成命。 韓國政府馬上將醫療危機警報級別上調至最高級「嚴重」,宣稱會以司法及行政手段懲處不復工的醫生,包括未服兵役的醫生會被即時徵召入伍。3月1日是死線,返回崗位的醫生很少,韓國保健福祉部宣布違反政府復崗命令的醫生會受到處分,至少吊銷3個月醫師執照,連帶不能滿足專業研修時間,取得專任醫生資格的時間將推遲1年以上。政府並聲言會以司法程序對付怠工醫生。 是次對峙可以視為2020年醫生團體抗爭的下集。當年醫生團體反對醫學院學生增額和設立公立醫學大學政策,大韓醫師協會發起無期限總罷工,政府在新冠疫情壓力下暫緩議案。 雙方理據 住院醫生是醫院服務前線運作的主力,集體辭職和罷工使大量手術被取消,因服務停擺而失救的新聞也陸續出現,民情多支持政府。有分析說,韓國會於本月舉行國會選舉,尹錫悅總統所屬政黨國民力量在國會議席佔少數,最大反對黨共同民主黨反而佔國會過半數,掣肘施政。尹錫悅總統就任兩年,民意支持度只得36.2%。這次重手增加醫生供應可以爭取選票。2020年時共同民主黨文在寅政府推動醫學生擴招失敗,今次尹錫悅若能壓服醫生,可以彰顯執政能力。(《星島日報》2月26日社論) 政治歸政治,從醫學倫理角度看,醫生很難提出有力理據來支持這種程度的抗爭,因為明顯會危及病人。 問題是,今次全國八成住院醫生參與集體辭職罷工,實習醫生至專科醫生的年齡差距接近10歲,難道整個世代的醫生都欠缺醫學倫理教育?皆自私自利?高級醫生和教授都支持年輕醫生的行動,也是不顧病人死活嗎? 政府提出的理據容易明白。韓國65歲以上國民佔總人口的比例目前已達19.1%,預計2050年65歲以上人口比率將超過四成,成為全世界國民平均年齡最老的國家之一。政府說,到了2035年,65歲上人口將比現在增加七成,估計導致國民住院總日數增多45%,門診需求增加13%。此消彼長的是,韓國醫生的平均年齡不斷上升,年輕醫師的比例持續減少,60歲以上之資深醫生數目卻颷升。韓國醫學院招生人數從千禧年至今都未曾增長過,若不果斷行動,韓國醫界將因為退休潮與醫生高齡化而出現嚴重的人才缺口。 相比之下,醫生團體抗爭的理據就複雜得多。例如說,城鄉醫療差距與個別專科醫生不足問題,癥結在於韓國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源分配不均,城市與醫學美容相關的專科醫生收入高,鄉郊普通科醫生收入低,形成長期的城鄉醫療差距。醫院制度也畸型,全國有醫生十多萬,100間醫院的海量工作全落在工時超長薪酬低的一萬多名住院醫生身上。政府長期無視改善工作環境的訴求,今次斷然單方面大增供應,完全不予談判議價餘地,才會觸發年輕醫生史無前例憤怒大爆發。 難處是,即使前線醫生面對諸般不公平,憤慨有合理原因,也很難說服公眾,必須集體辭職抗爭。 罷工合理嗎? 道理屬誰?現今AI對什麼都能給出像樣的解答,我請教入門級的Claude-3-Sonnet,醫生罷工有可能合理嗎?它的回答像香港以前「通識科」,正反兼顧,持平分析。它說醫生罷工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平衡多方的權利和利益,包括醫生、患者和整個社會。支持醫生罷工的論點有:一、其他談判手段失敗,罷工可能是最後手段;二、改善工作條件和解決醫生的擔憂,最終可以帶來更好和更可持續的醫療系統;三、與其他勞工一樣,醫生有權進行集體談判和勞資行動。 反對醫生罷工的論點包括:一、對患者的潛在傷害,中斷照顧可能導致併發症甚至生命損失;二、違反將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專業和道德義務;三、侵蝕公眾對醫療行業和醫療系統的信任。 總結:罷工應該是最後手段。即使在某些情況下,罷工可能被認為是必要和合理的行動,亦必須制定應急計劃,確保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患者的影響。 生成式AI不能具體分析時事。在韓國醫生抗爭一事,政府之前完全不予談判商討空間,也許醫生認為集體罷工已經是最後手段,但一下子去盡,明顯沒有顧及病人,亦沒考慮對必要的醫療服務包括緊急服務的衝擊,這是未充分思量醫生對病人是有「受託責任」(Fiduciary duty)。
[End-of-Life Seminar Series] Medical Assisted Dying in New Zealand

Come join us at our hybrid Seminar on Medical Assisted Dying in New Zealand which will be held on 19 March 2024 (Tuesday) at 4pm (Hong Kong Time) / 9pm (New Zealand Daylight Time) / 4am (Eastern Daylight Time). [End-of-Life Seminar Series] Seminar on Medical Assisted Dying in New Zealand Date: 19 March 2024 […]
Seminar on Genetic Testing of Children for Adult-Onset Conditions (co-organized by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and Hong Kong Children’s Hospital)

Prof. Josephine Johnston,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The Hastings Center, US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Bioethics Centre, University of Otago, New Zealand delivered a talk on “Challenges to the Rule: A New Zealand Case Study” at the Seminar on Genetic Testing of Children for Adult-Onset Conditions which was co-organized by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and Hong […]
我們有可能冒犯不存在之人類嗎?鍾偉岸博士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4.03.2024)

鍾偉岸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我們有可能冒犯不存在之人類嗎? 2021年,英國一名叫Evie Toombes的患有脊柱裂之女孩,狀告她母親的家庭醫生,引發熱議。 脊柱裂是一種先天性疾病,屬於神經管發育缺陷。當醫生發現備孕中的父母有機會將此疾病遺傳給子女時,應及時建議他們適當推遲受孕時間,並服用葉酸來避免這一情況發生。然而,Evie母親的家庭醫生忽略了這狀況,並沒給出相應醫學建議,導致Evie在出生後患有脊柱裂,不能跟正常人一樣生活。所以,Evie在20嵗時告該醫生犯下了醫療疏忽,並要求取得賠償。當地法官肯定了Evie的訴求。 以上稱為Evie Toombes案例。 Jeff McMahan 教授之不同見解 在中文大學2023年11月28日舉行的Lanson Lecture之中,Jeff McMahan教授對Evie Toombes案的判決給出了不同見解。 McMahan教授指出:「如果Evie母親的家庭醫生正確地給出醫療建議,那麽她將推遲受孕並且生下一個和Evie完全不是同一個人的健康兒童。所以,如果沒家庭醫生的醫療疏忽,Evie這個人將不會存在。」 McMahan教授進一步指出:「家庭醫生不應該為Evie出生後發生的種種不便負責,因爲他既沒預料到Evie生下來是這個樣子,也沒故意造成Evie生命中的苦難。」綜上所述,Evie實際上是從家庭醫生的醫療疏忽中受益(從中得到生命),她無權向醫生索取賠償。該醫生的醫療疏忽僅僅違反了「最佳生命原則」:人類在繁衍下一代的無窮可能性中,我們有理由讓生命質量最好的個體來到這個世界,而非其他生命質量較次的個體來臨。 筆者有幸參加了McMahan教授的講座並且提出兩個疑問:「按照最佳生命原則,家庭醫生應該讓一個比Evie生命質量更好的個體來到世界。由於醫療疏忽,醫生剝奪了這個體來到世界的權利。醫生是否應該賠償這個可能存在的人(possible person)?因爲這個可能存在的人,實際上不能從醫生的賠償受益,我們是否可以套用政治哲學中假定同意(hypothetical consent)的辦法設想:這個可能存在的人,將他索取賠償的權利轉讓給Evie?」 McMahan教授回答:「我們不可能冒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所以都不能對一個不存在的人有賠償義務。」 思想實驗 設想一個跟Evie Toombes案完全相反的思想實驗。假定一對備孕的夫婦在做檢查時得知:如果不採取措施,他們生下來的孩子,將有99%機會得脊柱裂。 醫生强烈建議他們推遲受孕時間,並在此期間服用葉酸來避免這一情況發生。 這對夫婦沒聽從醫生建議,並堅持按照原計劃懷孕、分娩。最後,很幸運,他們生下一個健康的孩子。 在這個例子中,多數人都會認爲:這對夫婦忽視醫生建議的做法是錯的。這錯誤甚至比Toombes案中家庭醫生的醫療疏忽更爲嚴重。然而,他們錯在哪裏呢? 第一、夫婦沒冒犯已經出生的孩子,因爲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跟正常人一樣健康。按照McMahan教授的理論,大家甚至不能認爲讓這孩子承受脊柱裂的風險是一種冒犯,因爲如果這對夫婦推遲受孕,將是另一個而非這個孩子會來到這個世界。 第二、他們也沒冒犯醫生,因爲病人有權選擇聽從或者不從醫生的建議。在極端例子中,一些早期癌症患者選擇不聽從醫生給出專業有效的手術建議,而選擇自然療法,醫生仍然需要尊重病人決定。 第三、夫婦亦沒冒犯社會共同體成員,因爲選擇繁衍下一代完全是私人事務。他們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一個健康的新成員,所以沒增加社會負擔。 因此,按照筆者觀點,這對夫婦最後只能冒犯那99%概率可能帶著脊柱裂來到這個世界的孩子,儘管這孩子事實上並不存在。冒犯一個不存在的個體是有可能的,只要我們能夠合理地預見(reasonably foresee)這個體將會存在。 這對夫婦沒聽從醫生建議,所以能夠合理地預見他們會產下一個患有脊柱裂的嬰兒。 不過,這嬰兒擁有免於帶著病痛來到世界的權利,所以其父母對他做了不負責任的行爲。 結論 […]
預設醫療指示 市民應否即時訂立?鍾一諾博士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5.02.2024)

鍾一諾博士中文大學生命倫理中心聯席總監 預設醫療指示(簡稱AD)在香港的立法箭在弦上,相信會在不久將來完成。坊間對此法律文件已有相當討論,然而還存在不少疑問。本文試解答其中一條問題:AD立法後,是否每個市民都應該即時訂立? 坊間存在兩個對立的說法。一方面,有人認為臨終醫療或死亡的事不用多講,乃至不應多講,「到時才算」便是;另一方面,坊間亦有聲音呼籲市民及早訂立AD,未雨綢繆,甚至有團體提供一站式服務,為市民一併訂立AD、遺囑/平安紙、持久授權書等法律文件,協助市民規劃晚期人生。 作為一個認同AD的學者,我當然不同意要到臨終時才開始思考自己的臨終醫療及意願,因為有可能到了那時已經太遲。例如許多病人當知道自己身患絕症時,身心靈備受壓力,足以妨礙清晰的思考,遑論要訂立需要病人有充足精神行為能力的法律文件。 可是另一方面,過早訂立AD,文件亦有可能不適用於幾年甚或幾十年後所發生的實際情況,讓文件不能發揮應有效果。西方國家有不少實例研究指出,如果AD在訂立者還未發病時已經訂好,訂立者有機會不太掌握自己被診斷患上絕症或不能逆轉疾病時的實際情況,從而錯判自己在那預計情況下的真實意願。 自相矛盾? 一邊呼籲大家,不要等到自己患上絕症或不能逆轉疾病時,才思考臨終醫療及意願,另一邊廂又商榷過早訂立AD這做法,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我認為,兩者不一定有衝突。呼籲大家思考死亡及自己的臨終醫療及意願,並不等於叫大家立即訂立AD─這份對於一些具體情況之下有所規範的法律文件。 尤其一些較年輕、並未罹患絕症或不能逆轉之疾病的人,他們的意願經常會隨著時間、經歴有所改變;甚至有研究指出,一些病人竟不大記得他們未有病時所訂立的AD細節,以至當時立某些指示背後的考慮因素。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對於針對絕症或不能逆轉的疾病來說,訂立AD可能不宜早於確診患上這些疾病的時間,因為那並未能準確反映病人的實際病情預後,以至他/她在了解病情預後的情況下所持有的感受及想法。不過,這些外國經驗也指出一些例外 — 一般來說,如果希望提早為自己未來萬一發生的不能逆轉昏迷及持續植物人狀態訂立AD,爭議相對較少。與絕症或不能逆轉的生命受限疾病不同,不能逆轉昏迷及持續植物人狀態的病者,都對自己當時狀態沒什麼感知,而這些生存狀態亦沒什麼有意義的未來可言,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對他們自己進入這些持續狀態後的情況有一定了解,從而可想像到自己在那情況下的抉擇。 掌握情況 相反,每個絕症或患有生命受限疾病的病人,情況及嚴重性都迥然不同,其反應和感受可以很不一樣,而且這些或許隨著病情的發展一路改變,因此很難過早預計到,他們自己在未來那個需要執行AD的特定情況下會怎樣抉擇。 那麼是否除非患有絕症,任何人都不應為不能逆轉昏迷及持續植物人狀態以外的情況提早訂立AD呢?我認為未必,大前提是訂立者要能夠對於自己確診患上絕症或不能逆轉疾病後的情況,有相當了解和掌握,明白拒絕那些維持生命治療對自己的後果,並且能夠具體表達出自己在特定情況下(如病情到了末期)的醫療意願。 例如,一個年輕人因為家族的某遺傳病或者有高風險患上威脅生命的慢性病,他/她清楚了解和掌握那疾病所帶來的情況、明白拒絕維持生命治療對一己的後果、並且能夠具體表達出自己在病情到了末期時的意願,那我看不到理由要勸止他/她訂立AD。要實現這個大前提,醫生對訂立者健康情況的專業判斷是必要的。這亦解釋到為何香港這條法例訂明,訂立AD時,兩名見證人裏面其中一位必須是醫生。 兩個意涵 在普遍實施層面,以上的分析至少有兩個意涵: 首先,我不認為坊間團體所提供的一站式晚期規劃服務,必須要為客人訂立AD,因為正如上文提及,訂立AD的需要因人而異。若果這些坊間服務能夠由接受過相關培訓的醫生,幫忙評估客人訂立AD的益處及必要性,並為那些能夠得益的客人訂立,我相信能夠惠及公眾。所以,任何有可能需要為病人訂立AD的醫生都應接受相關培訓;政府可細想這政策方向。 第二,預早在患上絕症前,便針對未來假設會患病的情況訂立一份AD,並非一勞永逸的做法。正因為AD是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訂立前應該經過深思熟慮,而不是基於心血來潮的衝動或怕吃虧的態度。當然,基於此法例的「慎入易出」原則,訂立者以後也可以用口頭或書面方式,更改已訂立的預設醫療指示,所以公眾毋須過分憂慮。 儘管如此,我也不認為公眾需要等到自己確診患有絕症或不能逆轉疾病時,才開始思考臨終醫療及意願。有所準備,臨危才不亂;因此,我會鼓勵向公眾推廣更深入的討論。AD的推廣教育至為重要,與新法例之推行互相配合方可相得益彰。
Centre Co-Director Prof. Roger Chung Interviewed by Now TV 《經緯線》on Advance Directives

好生好死 Retrieved from YOUTUBE.COM (21 January 2024)
[For CUHK Staff & Students & Alumni] Movie Screening: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年少日記)

[For CUHK Staff & Students & Alumni] Movie Screening: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年少日記) (co-organized by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the Wellness and Counselling Centr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Date: 23 February 2024 (Friday) Time: 7:00 p.m. – 10:00 p.m. (including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Venue: Sir Run Run Shaw Hall, […]
為垂危病嬰「拔喉」— 英國法院的判決錯了嗎? 區結成醫生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8.01.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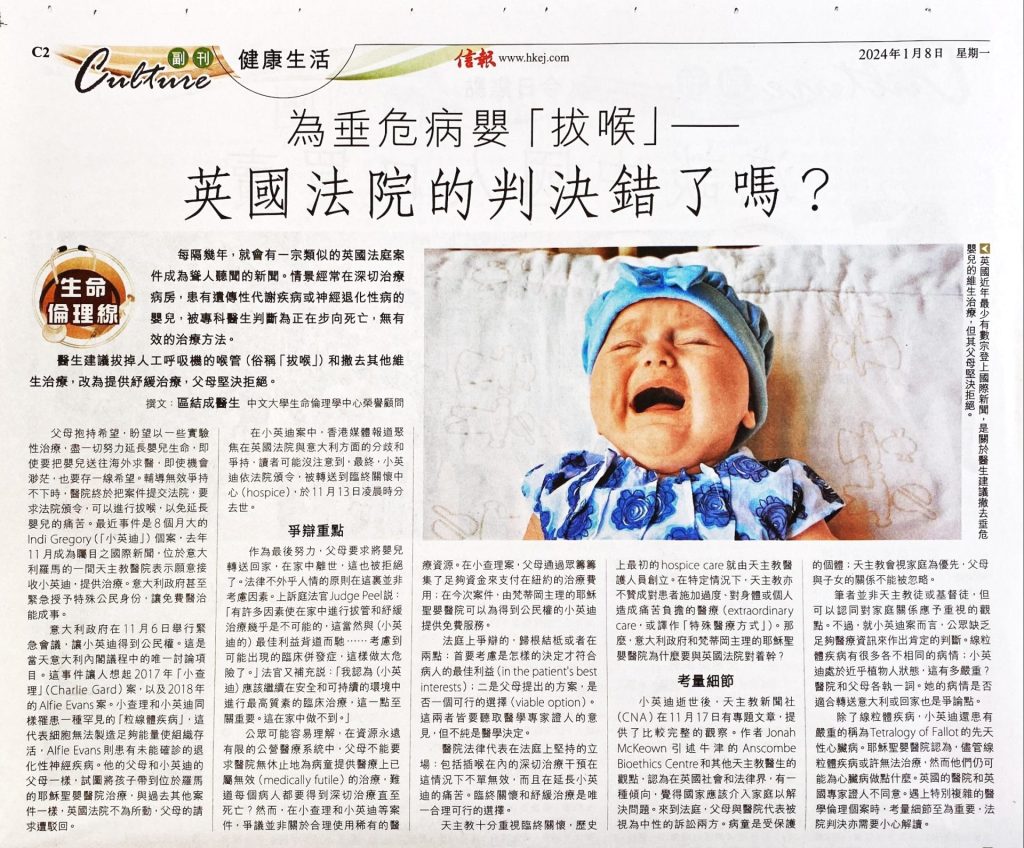
區結成醫生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 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宗類似的英國法庭案件成為聳人聽聞的新聞。情景經常在深切治療病房,患有遺傳性代謝疾病或神經退化性病的嬰兒,被專科醫生判斷為正在步向死亡,無有效的治療方法。醫生建議拔掉人工呼吸機的喉管(俗稱「拔喉」)和撤去其他維生治療,改為提供舒緩治療,父母堅決拒絕。 他們抱持希望,盼望以一些實驗性治療,盡一切努力延長嬰兒生命,即使要把嬰兒送往海外求醫,即使機會渺茫,也要存一線希望。輔導無效爭持不下時,醫院終於把案件提交法院,要求法院頒令,可以進行拔喉,以免延長嬰兒的痛苦。最事件是8個月大的Indi Gregory(「小英迪」) 個案,去年11月成為矚目之國際新聞,位於意大利羅馬的一間天主教醫院表示願意接收小英迪,提供治療。意大利政府甚至緊急授予特殊公民身份,讓免費醫治可能成事。 意大利政府在11月6日舉行緊急會議,讓小英迪得到公民權。這是當天意大利內閣議程中的唯一討論項目。這事件讓人想起2017年「小查理」(Charlie Gard)案,以及2018年的Alfie Evans案。小查理和小英迪同樣罹患一種罕見的「粒線體疾病」,這代表細胞無法製造足夠能量使組織存活,Alfie Evans則患有未能確診的退化性神經疾病。他的父母和小英迪的父母一樣,試圖將孩子帶到位於羅馬的耶穌聖嬰醫院治療,與過去其他案件一樣,英國法院不為所動,父母的請求遭駁回。 在小英迪案中,香港媒體的報道聚焦在英國法院與意大利方面的分歧和爭持,讀者可能沒有注意到,最終,小英迪英依法院頒令,被轉送到臨終關懷中心(hospice),於11月13日淩晨時分去世。 爭辯重點 作為最後努力,父母要求將嬰兒轉送回家,在家中離世,這也被拒絕了。法律不外乎人情的原則在這裡並非考慮因素。上訴庭法官Judge Peel說:「有許多因素使在家中進行拔管和紓緩治療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當然與(小英迪的)最佳利益背道而馳…。考慮到可能出現的臨床併發症,這樣做太危險了。」法官又補充說:「我認為(小英迪)應該繼續在安全和可持續的環境中進行最高質素的臨床治療,這一點至關重要。這在家中做不到。」 公眾可能容易理解,在資源永遠有限的公營醫療系統中,父母不能要求醫院無休止地為病童還提供醫療上已屬無效(medically futile)的治療,難道每個病人都要得到深切治療直至死亡?然而,在小查理和小英迪等案件,爭議並非關於合理使用稀有的醫療資源。在小查理案,父母通過眾籌籌集了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在紐約的治療費用;在今次案件,由梵蒂岡主理的耶穌聖嬰醫院可以為得到公民權的小英迪提供免費服務。 法庭上爭辯的,歸根結底或者在兩點:首要考慮是怎樣的決定才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in the patient’s best interests) ;二是父母提出的方案,是否一個可行的選擇(viable option)。這兩者皆要聽取醫學專家證人的意見,但不純是醫學決定。 醫院法律代表在法庭上堅持的立場:包括插喉在內的深切治療干預在這情況下不單無效,而且是在延長小英廸的痛苦。臨終關懷和紓緩治療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選擇。 天主教十分重視臨終關懷,歷史上最初的hospice care就由天主教醫護人員創立。在特定情況下,天主教亦不贊成對患者施加過度、對身體或個人造成痛苦負擔的醫療(extraordinary care,或譯作「特殊醫療方式」) 。那麼,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岡主理的耶穌聖嬰醫院為什麼要與英國法院對著幹? 考量細節 小英迪逝世後,天主教新聞社(CNA) 在11月17日有專題主章,提供了比較完整的觀察。作者Jonah McKeown引述牛津的Anscombe Bioethics Centre和其他天主教醫生的觀點,認為在英國社會和法律界,有一種傾向,覺得國家應該介入家庭以解決問題。來到法庭,父母與醫院代表被視為中性的訴訟兩方。病童是受保護的個體;天主教會視家庭為優先,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不能被忽略。 筆者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但可以認同對家庭關係應予重視的觀點。不過,就小英廸案而言,公眾缺乏足夠醫療資訊來作出肯定的判斷。線粒體疾病有很多各不相同病情;小英廸處於近乎植物人狀態,這有多嚴重?醫院和父母各執一詞。她的病情是否適合轉送意大利或回家也是爭論點。 除了線粒體疾病,小英廸還患有嚴重的稱為Tetralogy of Fallot的先天性心臟病。耶穌聖嬰醫院認為,儘管線粒體疾病或許無法治療,然而他們仍可能為心臟病做點什麼。英國的醫院和英國專家證人不同意。遇上特別複雜的醫學倫理個案時,考量細節至為重要,法院判決亦需要小心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