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之隔:病人知情權的差距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7.08.2018)

一河之隔:病人知情權的差距 「政治正確」令如今行文上要避免「中港兩地」的寫法,以免誤把香港劃在中國之外,但在討論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病人知情權的時候,難免會講「兩地差距」。過去四分一世紀,內地逐步改進有關病者知情權的規章和法例,兩地差距正在縮窄,但一河之隔仍有差別,香港的病人知情權以個人權利為起點,內地較多以家庭為本,遇上嚴重或緊急情況,近親主導醫療決定頗為常見,有時因非理性的決定引起悲劇,引發社會議論。在癌症病例,尤其多見向病者隱瞞病情。 改進起點 改進的起點,有人從1994年開始說,也有人從2002年說起。前者是針對醫療機構管理的行政法規,列明病者知情權包括了對自己的病情、診斷和治療知情;後者針對的是進行的醫療活動時,應當由病者本人簽署同意書。著手的方式是試行病歷書寫的基本規範,除了病者不具備行為能力之外,凡特殊檢查、治療、手術等,都要病人簽署。 這在香港看來十分基本,但當年在內地是很大的一步了。支持和理解的醫師認為,手術由病人自己簽字,是尊重知情權也是尊重人權,但新規定給醫生提出了新的課題,要讓病人明白手術的風險又要讓病人安心手術,並不簡單。過去習慣向病人隱瞞病情,如今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權,也需要一個過程。有些醫生,尤其是中醫,就懷疑新的規定有沒有好處,遺憾這忽視了簽字對病者心理的影響。 更嚴重的異議說,從法律上講,要病人簽字很公平,但同意書把手術中、手術後可能出現的嚴重情況一一臚列,好像要病人簽「生死契」,質疑是不是太殘酷?是否缺少了人文關懷? 無論如何,改革沒有止步。2009年頒布的《侵權責任法》,確認了病者知情同意權的獨立地位。「獨立地位」指的是相對於近親屬,病者有自主的權利。 病人自主大不易 在《中國法院網》讀到劉成瓊文章(24/12/2015) ,可見要讓病人有獨立的知情同意權是多麼不容易。尊重病人知情同意權的基礎是尊重病人自主,並不是簡單的手術前簽字制度,但社會文化並未配合,而且《侵權責任法》的條文也有一些含糊,確定性和適用性都意見分歧,例如一方面用多條條文規定了對病人知情同意權的重視,但也留有空間給病者近親屬行使多項病者的代理人權利。有一條規定是「不宜向病者說明的,應當向病者的近親屬說明」,但什麼是「不宜向病者說明」的範圍呢?這可以很窄理解,也可以演繹到非常闊。怕病人受不了壞消息,醫生就只與親屬溝通嗎? 在法例留有空間讓醫生酌情處理本身不是壞事,前提可能是專業判斷要有足夠的訓練,專業意見也要包含尊重病人。還有,要小心判斷家人又有沒有尊重病人意願。 在新近出版的書《如何走下去 — 倫理與醫療》我有一章〈病人自主與家庭參與〉,其中引述台灣學者李錦虹、洪梅禎,指出家庭未必都是和諧的,家庭功能也未必正常。因此,有些家庭情況很複雜,成員彼此的關係或許連好友都不如,亦可能充滿了各種負面情緒以及經濟上的利益衝突,可能要「健全的家庭」和「不正常的家庭」。 隱瞞病情徒勞 山東臨沂市人民醫院腫瘤科公維宏醫師的網誌文章很直接,有一篇乾脆起題目為〈癌症:家屬對病者隱瞞病情 既不科學也徒勞〉。文章引述多篇國內外調查,說明癌症病者大都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並非西方奉行個人主義的社會才是這樣,在日本,一項福岡大學組織的調查顯示,85.7%的被調查日本癌症病者希望獲知自己的病情資訊。在中國內地,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進行了一項對1023名中國癌症病者及家屬的調查,90.8%的被調查中國癌症病者認為應該讓早期癌症病人知道病情真相,60.5%的被調查癌症病者認為應該讓晚期癌症病人知道病情真相。 公維宏認為,若醫護人員無法向病者坦白講解病情,也就無從向其提供有針對性的心理支援,結果會進一步加重了病者的心理負擔。長期對癌症病者隱瞞病情也是不切實際的:病者總能從蛛絲馬跡中得知真相。對癌症病者一直隱瞞病情,有如於導演一場長期、全天候的話劇:指望病者家屬、醫護人員乃至病者病友都要有高超的演技,天衣無縫地編排「善意的謊言」,顯然不切實際! 香港的問題 內地的規章和法例逐漸接近香港的病人知情權概念,不是學香港,只是採納了國際通行的尊重病人自主的價值觀。兩地長久以來有差距,也不一定是香港的思維更「先進」,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向來實施的普通法是以個人權利為本,久而久之成為社會文化。即使如此,在實際操作上,家人仍有很大的發言權。 前面引述劉成瓊的文章,對內地醫療同意書的實踐情況有直率的批評,其實香港在使用醫療同意書的時候,也有不理想的情況。劉成瓊對內地醫療的具體批評同樣可以套用於香港:醫護人員在工作上履行告知病人的職責,但有時不免流於形式化機械化,例如根據標準格式「照本宣科」,簡單複述,忽略實質的交流過程。另一現象是,為要減少法律風險,同意書的告知的範圍日漸擴大,涵蓋併發症的風險越來越多,病人吃不消。香港的「問題」可能還在於:現有方式「行之有效」,再思量改進的動力相對小。
An Ethically Indefensible Plan for Biobanking Consent: A Cautionary Tale from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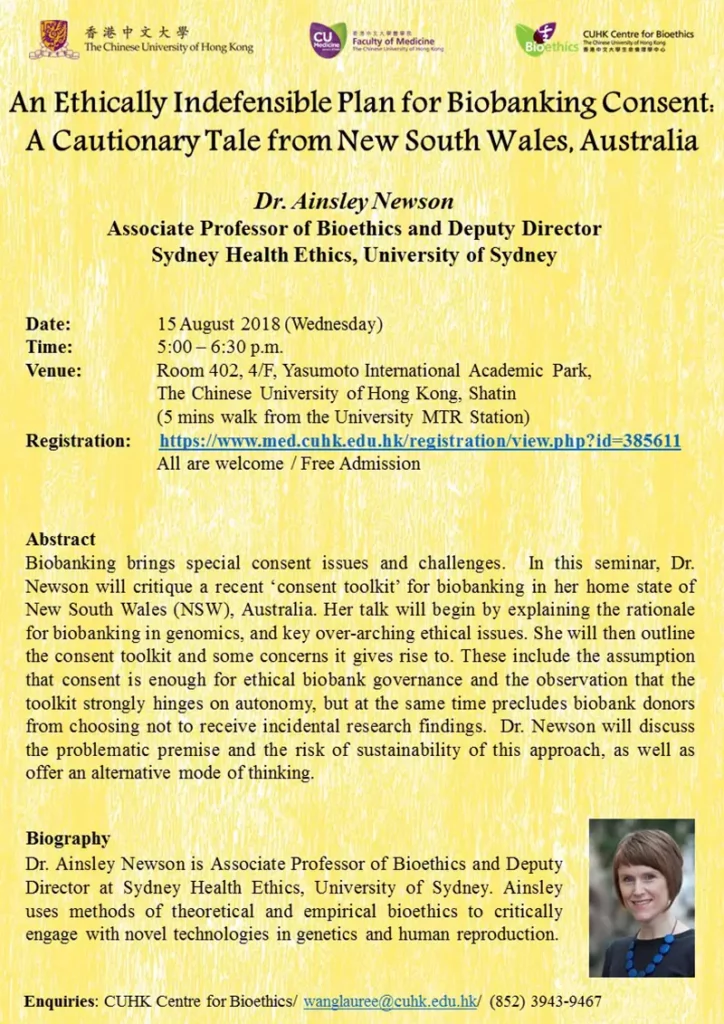
Date: 15 August 2018 (Wednesday) Time: 5:00-6:30 p.m. Venue: Room 402, 4/F, Yasumo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Dr. Ainsley Newso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ioethics and Deputy Director at Sydney Health Ethics, University of Sydney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Flyer: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如何走下去 — 倫理與醫療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30.7.2018)

如何走下去 — 倫理與醫療 醫學倫理的傳統,在西醫常上溯至「希氏誓章」(Hippocratic Oath),來到現代則更新擴充為各式專業倫理守則。傳統上,專業倫理的關注在三個範疇:醫患關係中的操守、與同儕的專業及利益關係,以及業務推廣的規範。醫生在現代社會既被視為精英階層,人們可以合理地期望醫學專業對社會能有更廣闊的關懷與擔當,例如關注社會公義和可持續發展。 香港的醫療制度能否持續發展,長期為市民提供可靠的、有質素的服務,老實說令人有些擔憂。醫院的服務常處於極為緊張的狀態,尤其在公立醫院,急症室與病房常如戰地,有時被譏為像「第三世界國家地區」。其實私營醫療的服務亦十分緊張,預約私家醫院的病床和手術室並不容易,而高昂的高科技醫療費用令一般中產階層也難以負擔。 何謂有質素的醫療服務?依2001年美國Institute of Medicine的界定,這應符合六個特徵:及時、安全、有效、高效率、公平、以病人為本。香港醫療算是「高效率」和「公平」;「安全」及「有效」程度不過不失;至於在「及時」和「以病人為本」兩項就未及格,深層原因關乎資源不足,更關乎我們這並不十分健康的醫療文化和醫療生態。 倫理與醫療唇亡齒寒 上月本欄談論「過度醫療」,指出「濫檢查、濫診治」不單對病人造成身心負擔,也是在浪費地球資源。而且,在財政資源總是有限的制度底下,醫療行為本身也是服務上左支右絀的成因。不少人以為,只要增撥資源,以增加人手和引進更多高科技便可以解決問題,但是,社會可以用在醫療的資源始終有限,難以應付所有人的需要,哪麽誰可以優先得到服務?若要增撥資源,錢從何來?誰要多付?誰得到補貼?要處理資源有限的問題,始終要討論如何公平地分配醫療資源和融資的責任。這就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倫理問題。 本文作者最近合編了一本文集,從醫療倫理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新書剛在香港書展面世。書名就是《如何走下去—倫理與醫療》。 有質素的服務需要資源,更根本的是依靠醫學專業的倫理,包括如何處理好醫患關係等等,處理得不好的話,自然影響服務質素,病人與公眾便不能滿意。良好管理和專業訓練可以提升和維持質素,但醫患關係常有更深一層的倫理問題,而且亦受到資源和制度制肘;反過來,缺乏信任的醫患關係亦會令資源短絀和公平分配資源的難題更加嚴重。倫理與醫療的關係,在關鍵處可以說是唇亡齒寒。 文集探討的另一個醫療倫理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醫護人員、病人和家庭的關係。當各方意見互相矛盾時,如何解決?一個解決辦法便是採納「以病人為本」的知情同意原則,即是要求醫護人員要令病人充份了解各項治療方法的好處和風險,從而作出自己的決定,但是醫療資訊往往很複雜,病人無法全面了解,詳細解釋亦需要很多資源和人力,機械式提供複雜資料更會引發其他問題。一個解決方法是給醫療人員更大的空間,自主地協助病人作決定。 醫療質素無疑有賴於社會能否給予專業自主和自我監察的權利,話雖如此,病人亦不可以無條件地信任,若果不對專業自主權利作適當的限制,就未必保障到病人的福祉以及公眾利益。如何取得一個平衡,不是簡單的倫理問題。除以上之外,醫護人員、病人和家庭的倫理關係問題還會以其他形式出現,對此文集均作探討。 在各個醫療專科範疇提供優質素的服務時,亦會遇到獨特的倫理問題。香港面對日益嚴重的老化問題,對醫療資源構成更大壓力,但是把老人服務當成一個包袱,亦是否公平和合理嗎?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安樂死和協助病人自殺在香港是不合法的,那麼有什麽其他合乎道德又合法的方法令臨終病人能夠更安祥和有尊嚴地渡過人生最後的階段呢?至於兒科病人,家長在一般可以為子女作最終醫療決定,但是,如果決定明顯違反病人的最佳利益,又或是病人的心智已成熟到一定程度而反對決定,醫療人員應該怎樣處理?香港正面對器官供應以作移植用途嚴重不足的情況,政府最近向市民就預設默許機制作諮詢,採用這方法會引發什麽道德爭議呢? 除了以上範疇,文集還有探討處理醫療事故、提供精神科服務、新生兒基因篩選、引進高科技和推行公共衛生政策時遇到的倫理問題。 好好想一想 我們要好好想一想,當醫療文化和醫療生態有病,受害的不只是病人,醫學專業本身亦會岌岌可危。因為醫療可否持續健康地發展從來也不單單是錢的問題,它與醫學專業的倫理是相關連的。倘若專業倫理把持不住,「過度醫療」泛濫,或不堪服務量壓力令疲憊塞責心態蔓延,那麼無論如何以嚴懲手段對付,也不能令良好的醫療服務持續發展。反過來,當醫療制度失衡,專業精神也就面臨被侵蝕磨損的危機。
CUHK-Columbia University Master of Science in Bioethics Scholarship Programme 20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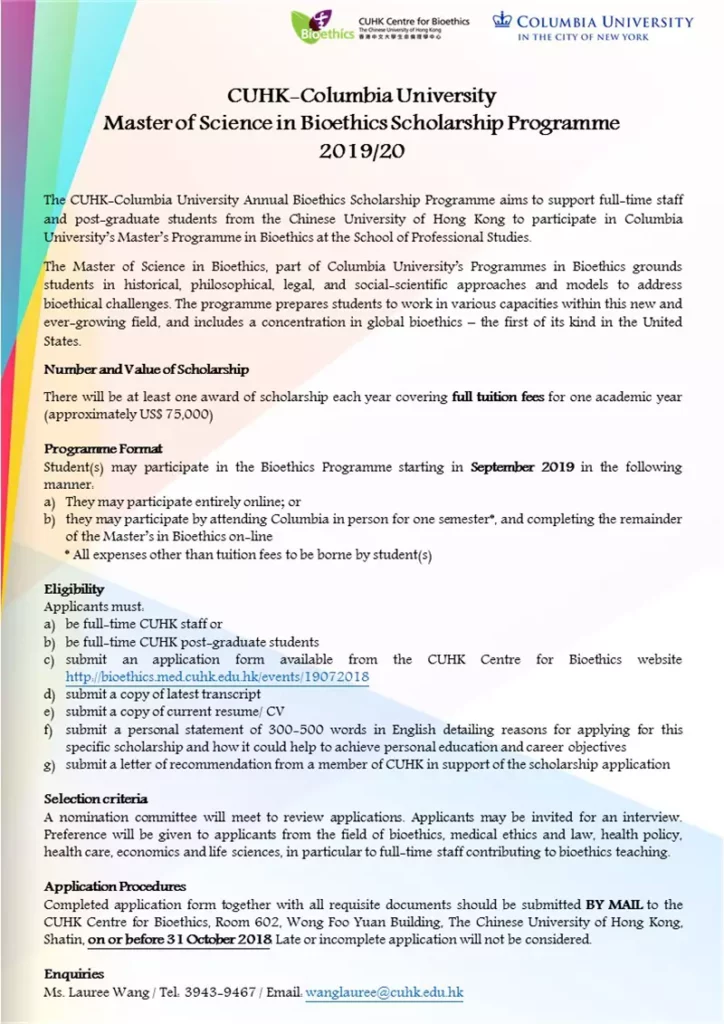
The CUHK-Columbia University Annual Bioethics Scholarship Programme aims to support full-time staff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Columbia University’s Master’s Programme in Bioethics at the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Bioethics, part of Columbia University’s Programmes in Bioethics groundsstudents in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legal, and […]
Centre Director Interviewed by HK01 on Young Living Liver Donor

【專訪】中大學者冀為港人倫理學補課 撐鄧桂思女兒捐肝對或錯?(HK01 社會新聞 08.07.2018) 本港的政策討論講求「明碼實價」,討論能為持份者帶來多少利益與損失。去年肝衰竭病人鄧桂思求肝,其未成年女兒求捐肝救母引伸的修例爭議也繞過倫理思考,直接討論法律可行性。 「我希望香港能以生命倫理作為其中一種施政的考慮。」報章專欄筆名為「區聞海」的區結成,由公營醫院高層一職退下來並轉職當學者,擔當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這一年多來筆桿繼續舞動,就世界大事作深度倫理分析。區結成自言不具野心,只是希望為香港補習生命倫理課,也讓生命倫理視角慢慢摻入政策考量的籃子裡。 以筆名「區聞海」寫作專欄和出書而為人所熟知的區結成,去年於醫院管理局退休,換了個身份到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擔任總監後,也換了個筆名,以真實姓名在報章撰文論述各式各樣的生命倫理議題,由動物權益、墮胎、安樂死、器官捐贈到基因編輯通通有涉獵,為了一個信念:幫香港補課。 「香港素來在中國有這樣的角色,對國際上發生的事更靈敏、看得更立體,但在生命倫理上未見有這樣角色,所以我希望幫香港補課。香港的生命倫理討論很多時停留在學院內,但如果只流於英文世界不能夠普遍,我希望生命倫理能與社會發生關係、入世,令香港政府、民間也好,多一個角度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討論。而不應是世界向前走很多步,不知不覺香港還未向前走。」區結成 去年「鄧桂思修例事件」正正反映生命倫理視角往往在香港政策討論上缺席。好媽媽鄧桂思去年4月因急性肝衰竭急需換肝續命,其長女Michelle希望捐肝救母,但因尚有3個月才滿18歲而被院方拒絕。事件感動民主派與建制派一度計劃合作提出緊急修訂法例,讓Michelle合法捐肝,最後因有熱心市民捐活肝,毋須為此緊急修例。 政策討論少了生命倫理考慮? 區結成說,當時政客集中討論法律上緊急修例的空間、如何免除醫生的法律責任等,少了生命倫理作為其中一種考慮,「從一個人的角度看,一定希望破例讓Michelle捐肝給媽媽,媽媽快死了難道不讓她捐嗎?」 然而,捐肝的死亡風險為0.5%,如果真的修例降低捐肝年齡,區結成擔心,有未成年少年因家人悲痛受壓力要考慮捐器官,與社會上保護兒童的概念相違背,區認為,不容易有可以說服所有人的立場,但也不能單純從個人自由和權利看,也不能因為單一個案感人而支持整個政策。 「做生命倫理,與我希望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有關。」區結成 區結成說,未有偉大使命要改變香港社會,甚或成為本港權威的生命倫理顧問,也不是為學科爭取地位,而是希望提高香港關心倫理議題的文化素養,讓社會在不同議題上留意多一些角度。 區結成計劃製作高中通識補充閱讀材料 除了「筆戰」,區結成也希望為中學生補習生命倫理。區結成閱讀過坊間教學生通識考試回答倫理問題的「雞精」材料,大意是教學生先定義安樂死,再列出贊成和反對的理由各5個,背誦並臚列這些理由取分。但區結成認為,生命倫理討論背後蘊含價值觀、政治現實等,不單是臚列贊成和反對的理據各三個「打和」,而是透過正反討論來分辨並找到較合理的理據。 區結成透露,正與出版社洽談合作製作高中通識補充閱讀材料,助學生在生命倫理上作聚焦且有層次的討論。 Retrieved from HK01.COM (8 July 2018) DisclaimerAll views 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various interviews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only,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r opinions of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過度醫療是什麼問題?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5.06.2018)

過度醫療是什麼問題? 近年各國醫學界日益關注過度醫療帶來的問題。過度醫療造成資源浪費,社會被醫藥化也是焦點。在這個課題,英國醫學雜誌是表表者,十多年前便問有否過度診斷,現在已能力舉數據和實例,確認過度醫療的確存在,呼籲醫學界要扭轉這趨勢,在過度與不足間取得平衡。美國醫學會雜誌也加入戰團,提「少即是多」的概念;也有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此為主題,今年的會議在赫爾辛基舉行。 過度醫療包括過度診斷、化驗和治療,令原本沒病的轉瞬間被診斷患病,要接受藥物及其他治療。美國紐約心臟學會去年十一月單方面將血壓高的定義,從140/90重新定在130/80,就是近期的例子。「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的診斷,也遇類似情況。早年美國糖尿病協會就將糖尿病前期的診斷數值下限降低,空腹血糖值由6.1變5.6,糖化血色素值由6.0變5.7。有學者質疑,如果直接把標準套在中國,這改變會將把一半中國人界定變為糖尿病前期患者!其它妊妊娠糖尿病、過度活躍症、抑鬱等的發病率也可能因重新定義而大幅上升。這表示很多人要開始服藥,得益的是藥廠。地球資源有限,本來不須服藥者都來吃藥是無比浪費! 有人問,病向淺中醫,早診斷就能早治療,這不是醫患所共想嗎?若早知有讀寫障礙,施以有效的教學法,當然是好;問題的癥結是,何謂早診斷而不是過早,何謂正常不正常?若肯定病情會在短期內惡化,那是有意義的早診;但對某些病而言,正常不正常的界線比較模糊。舉甲狀腺乳突癌為例,隨醫療強調標準化和指引化,若你的甲狀腺增大,在美國會為你先作超聲波檢查,看有否結節,再在超聲波導引下用幼針抽組織化驗,細小如2mm的結節都可以檢測到。從1979 到2009這三十年間,美國的甲狀腺乳突癌發病率上升三倍。癌病在早期就被發現切掉,但死亡率卻維持不變。從研究所得,細小的甲狀腺乳突癌是驗屍常見的附帶發現,當中許多終生都不會惡化。 乳癌的篩查更具爭議性。在上世紀末,幾個國家都開展乳癌篩查工作,令乳癌的數字直線上升。以常理推斷,篩查能檢出早期癌症,防止其惡化而奪走病人生命,若篩查做得好,那晚期癌症的機率理應逐漸減少,事實並非如此。顯然我們仍未充份掌握早期乳癌病變的自然發展。當中有些會惡化,但亦可能終生不會再變大,甚或縮小。若我們將後者都當作普通癌症醫治的話,那是過度診斷過度治療。 其他例子還有主動脈瘤的定義。一般來說,若瘤的直徑達5cm,就要接受手術。把主動脈瘤的定義下降或能防止某些病人死亡,但亦令更多人接受手術。 治療本身有風險,過度診斷造成過度治療,後患更多。過度使用抗生素令細菌產生抗藥性大家都耳熟能詳。長者到公營門診看病,離開時拿大包小包的藥動輒十種以上,副作用可能不少;若毫無徵狀者因過度診斷動手術發生併發症甚至死亡,更是不值。 過度醫療現今已是世界現象,這不純是醫學課題,其中有制度、經濟和醫學倫理因素。在中國大陸,學者驚呼醫院以自身的經營業績為優先,在欠缺專業規範的醫療市場濫做檢查,用最最貴的藥用最好的儀器診治最輕微的病徵。在台灣,健保制度被濫用是焦點。 三管齊下求轉機 一般來說,私營醫療有較大的經濟利益誘因過度診斷和過度醫治,一些藥廠在市場推廣上推波助瀾。美國近年尤其關注一些「進取」的推廣,以病人倡導(patient advocacy) 為名,做勢行銷。 在公立醫院也有特殊的制度因素做過度的診斷。有前線醫生痛心反映,在「多些來密些手」的日常工作流程,時間是醫生最大的「成本」,隨手order tests太容易,例如例行快速測試見尿蛋白輕微陽性,不用想也可繼而抽血篩查各種可能性,其中一項驗血結果陽性,又衍生下一步的各種檢查。因為沒有時間按症狀採取觀察和逐步診斷,按本子漁翁撒網便最「保險」。其實也不單是醫療,在步伐急促的香港,「有殺錯冇放過」可能是一種普遍的處事心態。 前輩教授說,時間是最好的診斷家。合理觀察和逐步診斷往往能收到好效果。然而說到底,行醫治療要面對風險,對「邊緣個案」醫生能夠持保守觀望態度嗎?在當今容易訴諸法律的社會,沒有跟大隊做法的醫生,若治療結果不如人意,要承受被告上法庭的風險。面對治療的風險,醫生能對邊縁個案持觀望態度嗎?在當今容易訴諸法律的社會,沒有跟大隊做法的醫生,若治療結果不如人意,要承受被告上法庭的風險。 改變過度治療的積習並不容易。例如切除乳癌的手術,傳統方法是把腋下淋巴組織全部切除,造成十分麻煩的淋巴水腫併發症,要經過幾十年光景,到長期跟進病人術後達25年的一些論文發表了,手術方法才有所改變。在資訊透明發達的今天,引人新技術的速度越來越快,要等足夠數據證明新技術絕不容易。這還未討論到病人的角色。 害怕因走漏了不明顯的病例而要承擔不如意結果,在醫生和病人都是一種情意結。醫學在進步,日後或者有更準確的預測病變的知識和技術,但在此之前,醫學界和社會要正視過度治療的問題,從倫理、醫學和制度文化反思,三管齊下,才有希望在減風險與減浪費之間取得平衡。
「一視」與「同仁」:資助昂貴醫藥的兩種倫理想法 (《教區生命倫理小組通訊》09.06.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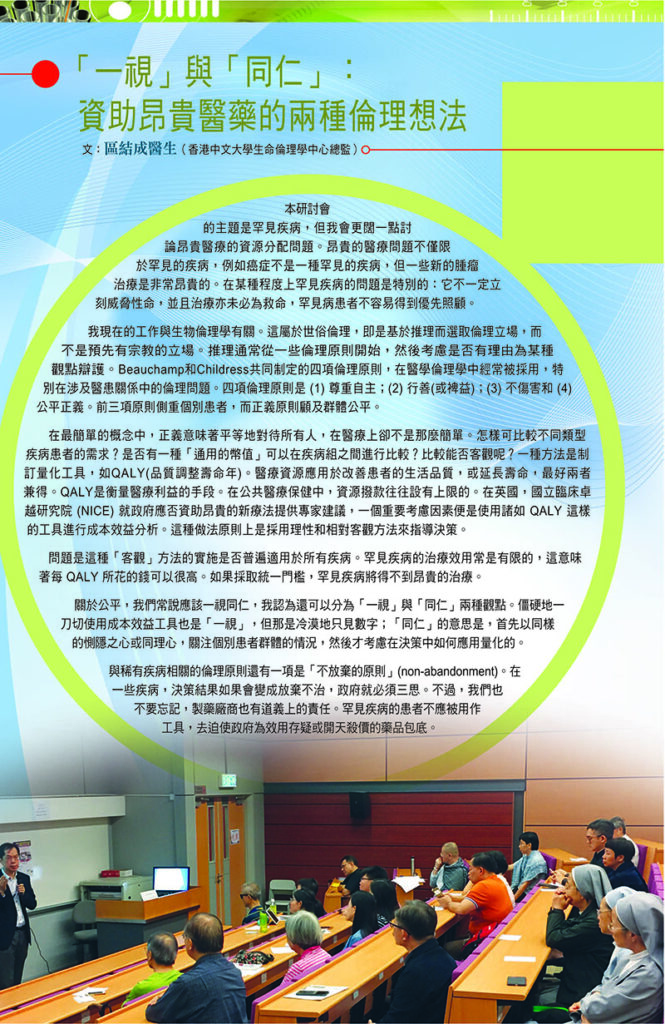
「一視」與「同仁」:資助昂貴醫藥的兩種倫理想法 本研討會的主題是罕見疾病, 但我會更闊一點討論昂貴醫療的資源分配問題。昂貴的醫療問題不僅限於罕見的疾病, 例如癌症不是一種罕見的疾病, 但一些新的腫瘤治療是非常昂貴的。在某種程度上罕見疾病的問題是特別的:它不一定立刻威脅性命,並且治療亦未必為救命,罕見病患者不容易得到優先照顧。 我現在的工作在生物倫理學。 這屬於世俗倫理, 即是是基於推理而選取倫理立場, 而不是預先有宗教的立場。推理通常從一些倫理原則開始,然後考慮是否有理由為某種觀點辯護。Beauchamp和Childress共同制定的四項倫理原則在醫學倫理學中經常被採用, 特別在涉及醫患關係中的倫理問題。四項倫理原則是 (1) 尊重自主,(2) 行善(或裨益), (3) 不傷害和 (4) 公平正義。前三項原則側重個別患者, 而正義原則顧及群體公平。 在最簡單的概念中,正義意味著平等地對待所有人,在醫療上卻不是那麼簡單。 怎樣何比較不同類型疾病患者的需求? 是否有一種「通用的幣值」可以在疾病組之間進行比較?比較能否客觀呢? 一種方法是制訂量化工具, 如 QALY (品質調整壽命年) 。 醫療資源應用於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或延長壽命,最好兩者兼得。 QALY 是衡量醫療利益的手段。 在公共醫療保健中,資源撥款往往設有上限的。 在英國, 國立臨床卓越研究院 (NICE) 就政府應否資助昂貴的新療法提供專家建議, 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便是使用諸如 QALY 這樣的工具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這種做法原則上是採用理性和相對客觀方法來指導決策。 問題是 這種「客觀」方法施是否普遍適用於所有疾病。罕見疾病的治療效用常是有限的, 這意味著每 QALY 所花的錢可以很高。 如果採取統一門檻,罕見疾病將得不到昂貴的治療。 關於公平,我們常說應該一視同仁,我認為還可以分為「一視」與「同仁」兩種觀點。僵硬地一刀切使用成本效益工具也是「一視」,但那是冷漠地只見數字;「同仁」的意思是,首先以同樣的惻隱之心或同理心關注個別患者群體的情況, 然後才考慮在決策中如何應用量化的。 與稀有疾病的相關的倫理原則還有一項是「不放棄的原則」(non-abandonment)。 在一些疾病,決策結果如果會變成放棄不治,政府就必須三思。不過, 我們也不要忘記, 製藥廠商也有道義上的責任。罕見疾病的患者不應被用作工具,去迫使政府為效用存疑或開天殺價的藥品包底。
百歲求死:了結生命是權利?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1.05.2018)

百歲求死:了結生命是權利? 當著名的植物學家及生態學家David Goodall年初在104歲的生日會公告他預備從西澳珀斯遠赴瑞士尋求了結生命,他的故事和對安樂死的主張同時成為環球熱話。倡導自願安樂死的組織Exit International為他眾籌2萬澳元旅費,有220多人支持。組織也為他安排傳媒訪問,並有護士陪伴上路。事先張揚的安樂死旅程也用來批評澳洲政府對安樂死的政策。這場示範式旅程是一個受人愛戴、在社會有榮譽的老人能送給倡導安樂死組織的一份大禮。 澳洲曾多次辯論應否讓安樂死合法化,至今只有維多利亞省容許協助自殺,範圍限於患有絕症、預期壽命少於6個月的病者。Goodall老先生沒有身患絕症,並不符合資格。去年他在獨居的家中跌倒,沒有骨折但倒臥地上兩天後才被發現。在一些訪問中他說在跌倒後住醫院感到人生已無尊嚴,不願意活下去。他在20多年前率先加入Exit International成為會員,認為自願安樂死應該屬於個人權利。這一跌,令他決心在健康變壞之前尋求結束生命。 一些中文媒體誤把他尋求協助自殺的決定理解為寂寞可憐老人厭世的辛酸故事;有些英文媒體記者在字裡行間顯露出對死亡自主的認同,比較完整而立體的素描見於5月5日澳洲ABC新聞記者Charlotte Hamlyn的專題報道〈The Last Move〉。Goodall不是沒有非常愛他的親友,他只是異常地珍惜個人獨立自主,堅定捍衛死的自決權利,不受限制。他的說法是,一個公民到了五、六十歲,已經回報了社會,此後他如何處理晚年生命就是個人的事。他不是主張別人結束生命,但認為如果有人想這樣做,誰也不應干涉。 本文在5月9日晚上動筆,這時Goodall已抵達瑞士Basel,等候醫生評估確認是否合適進行協助自殺。 瑞士有三個施行醫藥協助自殺的機構,其中Exit只接受國民申請,Life Circle Clinic和更高調廣為人知的Dignitas Clinic會協助外國人進行自殺。為Goodall眾籌旅費和宣傳行動的Exit International 本身是倡議安樂死組織但不直接提供服務,它為Goodall安排在Life Circle Clinic結束生命。 Life Circle創辦人是Dr. Erika Preisig和Ruedi Habegger兩姊弟,他們曾協助自己的父親自殺。Erika Preisig曾為Dignitas工作,2011年自立門戶,成立機構Eternal Spirit,診所命名Life Circle。Habegger強烈批評澳洲不准許 Goodall在老家死亡,是等同「暴行」(atrocity)。這是重話 — 在歐洲,譴責納粹屠殺猶太人才用得上「暴行」字眼。 在1998年成立的Dignitas的創辦人Ludwig Minelli是個律師,言行出位,瑞士政府對其高調言論和Dignitas的封閉式財務管理向來不滿,對他向外國推廣有如自殺旅遊(suicide tourism) 的「服務」更感尷尬;Minelli則對政府的逐步加強監管嗤之以鼻。他堅持,個人自決死亡是所有人應爭取的最後一項人權(the last human right) 。 瑞士政府尤其關注從外國來尋死的人,一向不在瑞士求醫,下機後到自殺診所接受「評估」只是形式上依法。Dignitas有些客人從入境到接受評估到協助自殺死亡不足24小時就完事,瑞士政府覺得太草率,在2007年12月收緊要求,規定需要兩名醫生分別進行評估。這惹怒了Minelli,他反應快而且極端:一連四次使用氦氣進行協助自殺,這是提醒政府,他不需要靠醫生處方藥物也可以進行業務的。 2008年瑞士發生一宗醜聞:一個救援組織的潛水人員在蘇黎世湖打撈他們船隻掉落的物件時,意外發現水底有大批骨灰罌,警方證實骨灰罌裡頭裝的是人類的骨灰,而罌上面印有Dignitas診所常規使用的火葬場的商標。Dignitas位於蘇黎世湖附近,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來自指向這些骨灰罈就是所丟棄的,但有前員工指它多年來一直有這樣做,至少丟了300個骨灰罌在湖裡。 Exit International創辦於1997年,創辦人Dr. Philip Nitschke 是醫生,年紀輕輕從醫學院畢業不久已經為安樂死而著迷,尤其嚮往美國第一個公開協助病人自殺的醫生Dr Jack Kevorkian和他設計的自助「死亡機器」。 Dr. Nitschke 與夥伴共同創製新型的自殺機器Sarco,可以用3D打印技術低成本自製,躺進去按下死亡鍵,膠囊內會釋放氮氣令使用者缺氧而死。今年在荷蘭展出的Sarco膠囊形狀像太空艙,底座可以重複使用,執行完安樂死後將膠囊連死者拆下就可以直接作為棺材入殮。Dr. Nitschke便是今次全力支持Goodall示範尋死之旅的主角。他的主張是「每一個理性的成年人都有選擇安樂死亡的權利」。 Dignitas創辦人Minelli 和Exit International創辦人Dr. Nitschke […]
Journal Club: Artificial Cognition and Clinical Medicine: What are the Ethical Concerns?

Date: 11 May 2018 (Friday) Time: 5:00 – 6:30 p.m. Venue: Room UG 01, Wong Foo Yuan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Ms. Stephanie Holmquist, a New York based bioethicist affiliated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Journals: Implementing Machine Learning in Health Care – Addressing Ethical Challenges Artic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vailable here Predicting the […]
Centre Director Quoted in a News Report on Medical Council Ruling

【紗布封喉亡】前線醫生聯盟發起簽名反醫委會裁決 日內開記者會 Retrieved from HK01.COM (10 May 2018) DisclaimerAll views 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various interviews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only,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r opinions of the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