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闢倫理學蹊徑 卡拉漢拒受哈佛馴服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7.7.2017)

另闢倫理學蹊徑 卡拉漢拒受哈佛馴服 2015 年 10 月 15 日,哈佛醫學院Center for Bioethics請來有「生命倫理學之父」尊稱的Daniel Callahan (丹尼爾 · 卡拉漢,1930 – ) ,在公開論壇談他的回憶錄In Search of the Good: A Life in Bioethics。這也是回顧半個世紀生命倫理的探索。演講連答問超過1小時,85歲的Callahan思路敏捷,風彩依然 。網上可以看現場錄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B4mIQQZYE) 開場白,主持人笑問他:「你在書中談到早年在哈佛修博士學位,是糟糕的經歴,可否一談?」Callahan在 60年代在哈佛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當中的經歴令他意決不走學院哲學之路。他選擇做靠近社會議題的事,包括人口政策研究,寫文章關注避孕、墮胎等。對社會議題的關心始於畢業前,那時期他在天主教刊物Commonweal任編輯,特別關心社會、文化、價值觀的課題。 關於Callahan在哈佛的「糟糕經歴」,我會看作一個年輕學人拒絕被主流學院建制馴服的故事。Callahan承認在進哈佛之前,未有做好功課,完全不知道當時哈佛哲學系是什麼門路。這是哈佛哲學系獨尊牛津劍橋分析哲學的年代。傳統的人生哲學問題,例如生命存在的目的、善與惡、人性等,很多都被犀利的語言分析肢解,視為「偽問題」。Callahan卻是為了這些問題來修讀哲學的。在課堂上,教授認為他的問題不值得回答,他提出質疑,事後要到教授辦公室去談話。他的博士論文提案兩次被導師拒絕。 Callahan發現, 60年代的學術主流內,道德哲學只是邏輯理性的思辨遊戲。他自己的偶像卻是蘇格拉底,在市集廣場與雅典公民辯論哲學。 哈佛時期的Callahan也醉心宗教,哲學系的課堂令他氣悶,就跑去神學院旁聽,結論是:「神學家那兒有許多有趣的問題,卻沒有思考工具去處理;哲學這兒有各種思考利器,但一個有趣問題也沒有。」到他畢業後,70年代的哈佛哲學學者包括John Rawls卻重新關注人間的課題了,例如公義。 1969年, Callahan已是多個孩子的父親,39歲才來創業,與精神科醫學教授朋友Willard Gaylin 在所居的河畔小鎮Hastings-on-Hudson共同創辦一所獨立的民間倫理學研究中心Hastings Center。Hastings無疑是世界上第一所研究生命倫理課題的中心,畢竟Bioethics這個名詞還是在1970年才誕生的! Callahan在一篇文章說,創業之初,Callahan家中臥室便是規劃辦公室兼文具倉庫;Gaylin的房子則放置複印機和儲存文件檔案。但他們一開始便充滿信心,相信必會成功。他回想70年代的美國社會創業蔚然成風,Hastings算得上是開風氣之先,他不無自得地說:「稍後Steve Jobs 和Bill Gates也加入冒險創業潮流,我聽說他們也幹得不錯。」 在60年代末,他發表一系列從正反角度辯論墮胎的文章,超越了基督教保守派與自由主義個人權利對立的兩極思維,因而嶄露頭角。1972年Abortion: Law, Choice and Morality一書出版,奠定了他在生命倫理學的獨特地位。 生命倫理學並非普及的學科,怎會受公眾矚目?這是時代使然:二次世界大戰後生物學和醫學的飛躍觸發新興的倫理問題和社會爭議,有限資源承受不了昂貴的新醫學科技,全新的避孕與墮胎道德爭論撕裂社會;科學家也有困惑,像愛因斯坦量子物理理論造就可怕的核武器那種夢魘,會否在生物學重演?當人類基因結構被破解,優生學上的應用指日可待,既有的道德規範能適應未來嗎? 中國學者研究Daniel Callahan 書架上有一本Daniel Callahan 與Mark Hanson合編的The Goal […]
Journal Club: End-of-Life Decisions: Where Views Diverge

This event is by invitation only Date: 6 July 2017 (Thursday) Time: 5:00-6:30 p.m. Venue: Rm UG02, Wong Foo Yuan Building, CUHK Campus, Shatin Speakers: Dr. Derrick Au, Director, CUHK Centre for Bioethics Dr. Tak-Kwan Kong, Consultant Geriatrician, Department of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s,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Discussant: Prof. Julia Tao, Adjunct Professor, Office of the Provost, City University of […]
CUHK-Columbia University Master of Science in Bioethics Scholarship Programme 201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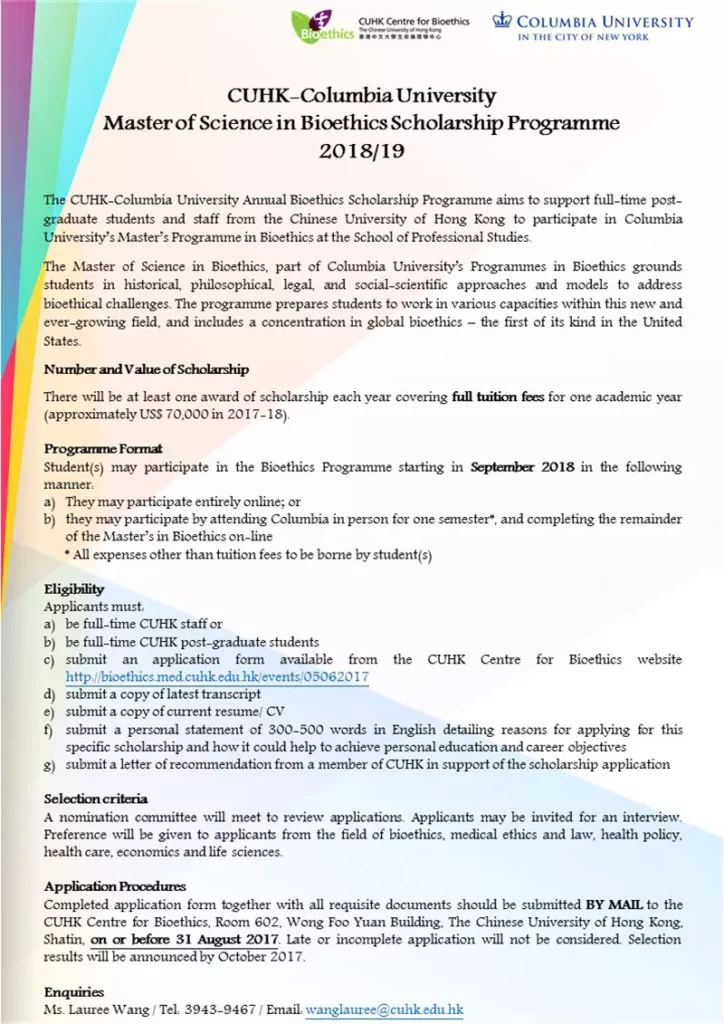
The CUHK-Columbia University Annual Bioethics Scholarship Programme aims to support full-time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staff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Columbia University’s Master’s Programme in Bioethics at the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Bioethics, part of Columbia University’s Programmes in Bioethics grounds students in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
倫理困惑:病人自主?老來從子?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2.6.2017)

倫理困惑:病人自主?老來從子? 醫學倫理有四條大家普遍認同也在應用的原則,列作首位的是「尊重自主」(respect for autonomy) 。病人有自主的權利,不單在倫理道德上要得到尊重,法律原則也是一樣,而且可能比倫理原則規定得更嚴厲。但是實際上,我們真有那麼尊重病人的自主嗎?如果尊重病人自主必然是優先考慮,那麼為何家人總在參與決定,甚或主導了決定? 近月來參與的好幾個研討會都在談這個問題。我離開臨床工作已相當時日,想知道前線醫生的看法。一個年輕專科醫生Carlton對我說:「在臨床工作上遇到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協助長者做醫療決定。」 我有點驚訝。比起傳媒和社會常在熱情關注的醫療事故焦點,這似乎完全是bread and butter的日常醫務,每天老人入院、老人出院,有如流水作業吧?困惑在哪裡? 往下再談,很多疑問還是與「尊重病者自主」相關,但在老年病人,矛盾又更尖銳一些。 Carlton說,毫無疑問,一個欠缺病人參與的醫療決定,算不上是好的決定。醫生不能亦不應完全替代病人去做重大的醫療決定,除了在緊急及生命攸關的情況(若病人沒有預先表達意願)。問題來了,誰說了算?醫生該找誰商討?困難之處,有時在決定本身:明明知道病人簽紙出院,自行回鄉終老是有危險甚至就是玩命,但他執意如此,醫生是否一句「尊重病者自主」就了卻責任?有時困難不在決定本身,而是做決定的過程充滿張力。在一個極端案例,長者病人的現任配偶與前度配偶的子女爭奪話事權,醫生變成家庭糾紛調解員? 在這種極端情況,反而可以向監護委員會(Guardianship Board)申請,指定一個法定監護人(legal guardian)。我以前當過監護委員會委員,知道若病人精神或神智上已無自行決定的行為能力,而家人爭執中的一方明顯不合理地損害病人的最佳利益,申請指定一個理性的法定監護人是有幫助的。這常常是在極端情況的最後一步,畢竟監護委員會也不能變成一般的糾紛調解員! 監護委員會更不適用於處理精神上仍有行為能力的病人。臨床所見,有些長者精神仍然健全,但在強勢話事的子女面前,可能不敢表達意願。 生命倫理學者討論「尊重自主」原則,往住會先退後一步,問我們的價值觀是什麼?如果中國文化的價值觀是重視家庭,那麼病人的意願應該放置在家庭福祉的較大範圍中來考慮?很有問題的家屬是少數。如果老人願意以家人利益為重,放棄對自己有益但對家人做成負擔的治療,那也是一種廣義上的「自主」?這乍看只是一種理論假設,在中國大陸卻是農村實況:一個家人重病,入城進大醫院求醫到底,全家的經濟可以陷入絕境。 在香港,討論焦點落在個人自主方面。例如:香港應否大力推動長者病人「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以便一旦他失去自決的行為能力,醫護人員可以尊重他的個人意願,不施行違反個人意願的侵入性治療(例如心肺復甦術)? 在法律上,自決權利屬於個人而非家人。但不少人認為,放棄維生治療不是只關乎個人,必須有家人參與。 卻亦有生命倫理學者提醒,不要隨意美化「家庭」這個觀念。病態的家庭和虐老的家庭或者是少數,但經濟和生活上依靠子女的老人是脆弱一群(vulnerable population) ,要小心保護他們個人自主的權利。事事聽從子女,表面看來自願,長者可能正在受苦。「老來從子」在現代社會無論如何也不再是應繼續提倡的觀念,文化價值觀是演進的,也應該演進。 持久授權自己信任的人 一個老人患腦退化並有吞嚥困難毛病,大部分時間清醒,有時神志昏亂,他年近百歲,因嗆喉吸入性肺炎出入了醫院幾次,終於一次嚴重肺炎兼昏迷入院,已經垂危。太太和子女一致清楚知道他的心意是平安地走就好,但主診醫生還是認為非得要輸液和用靜脈注射廣譜抗生素,治療多一輪才可決定放手。這是實例。 醫生有他的道理我很明白,但我個人有些期待,希望香港修訂法例,可以讓病人和長者訂立「持久授權書」(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授權範圍要能涵蓋個人照顧事宜的決定,包括健康和醫療照顧。 持久授權書是一種比較簡易的法律方法,讓授權人在精神上有能力行事之時簽立,把法律權限持久地給予另一人(受權人),在有需要時便可以代為作出法律上有效的決定。假設我最信任的是我的弟弟,我授權給他,到我變得精神上無能力決定的時候,他就可以有效地代表我,與醫生商討治療方案。 2011年7月11日,法律改革委員真的發表了報告書,建議擴闊持久授權書的適用範圍至個人健康照顧事宜。然而報告書的建議留了一手:受權人可以為授權人作出的健康照顧決定,不能涵蓋拒絕維持生命的治療。以上面的個案為例,注射抗生素也是維持生命的治療,即是仍然只由醫生決定。 或問:為何不選擇索性預設醫療指示,指定在某些情況下拒絕維持生命的治療?因為預設醫療指示時,很難預見到日後所有醫療情況。在不同情況底下可以用於維持生命的醫療干預手段真是數之不盡!而且,授權由自己信任的人作決定,並且預先向他講清楚自己對醫療的想法,會是比較人性化。 台灣走的是另一條路,在2015年12月18日制定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2016年1月6日公布,預計在2019年1月正式實施。這是亞洲第一部關於病人善終權利的立法。它的範圍不限於末期病患者,故此說是「亞洲第一部」。我尚在閱讀它引發的爭議。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7年6月12日,C2 )
Medical Science, Social Welfare, and Individual Lives: Integrating Competing Clai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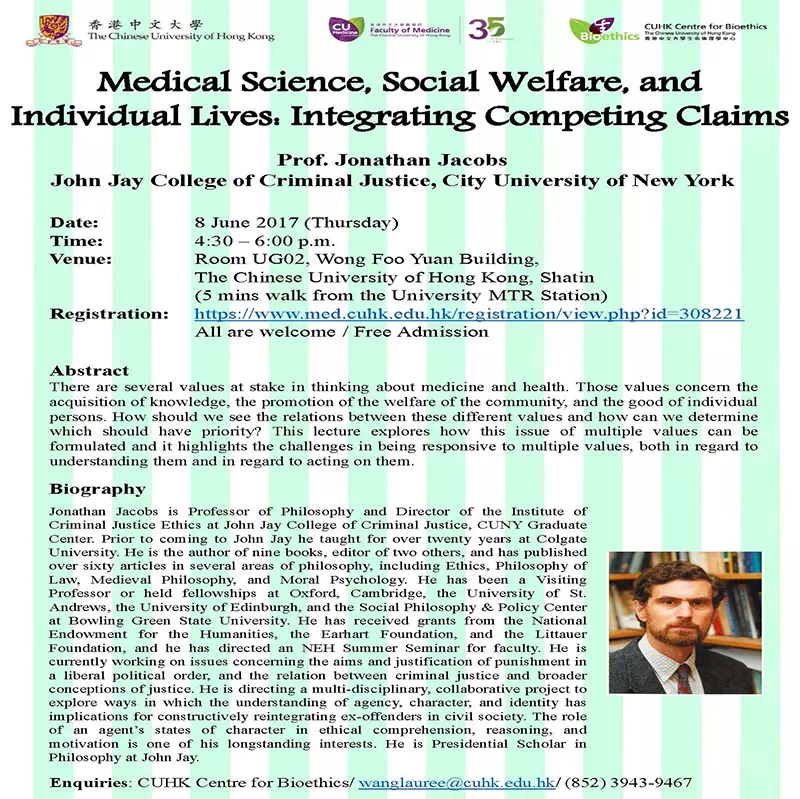
Date: 8 June 2017 (Thursday) Time: 4:30-6:00 p.m. Venue: Room UG02, Wong Foo Yuan Buildi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Prof. Jonathan Jacobs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Flyer: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Paper by Prof. Jonathan Jacobs – “Medical Science, Social Welfare, and Individual Lives: Integrating Competing Claims” Handout
Launch Ceremon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 and Public Lecture

Date: 2 June 2017 (Friday) Time: 11:45 a.m. – 12: 45 p.m. Venue: Kai Chong Tong,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entr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Shatin Transportation: Coach service will be arranged between CUHK campus and the event venue (please see details in the registration page)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Online registration will be closed on 31 May 2017) Language: English Flyer: Please click here […]
What Can Philosophy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Teach Each O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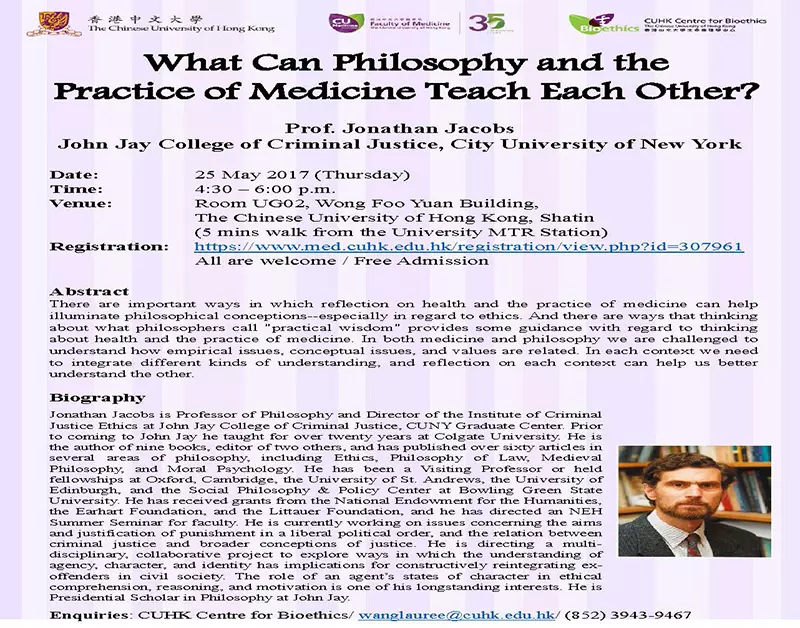
Date: 25 May 2017 (Thursday) Time: 4:30-6:00 p.m. Venue: Room UG02, Wong Foo Yuan Buildi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Prof. Jonathan Jacobs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Flyer: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Paper by Prof. Jonathan Jacobs -“What Can Philosophy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Teach Each Other?” Handout
Journal Club: Proxy Decision Making and Respect for Autonomy of the Elder Patient

This event is by invitation only Date: 18 May 2017 (Thursday) Time: 5:00-6:30 p.m. Venue: Rm UG02, Wong Foo Yuan Building, CUHK Campus, Shatin Speakers: Dr. Derrick Au, Director, Centre for Bioethics Dr. Ho-Mun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vent Recaps: Journals: “Beyond autonomy: diversifying end-of-life decision-making approaches to serve patients and […]
Consenting to Your Own De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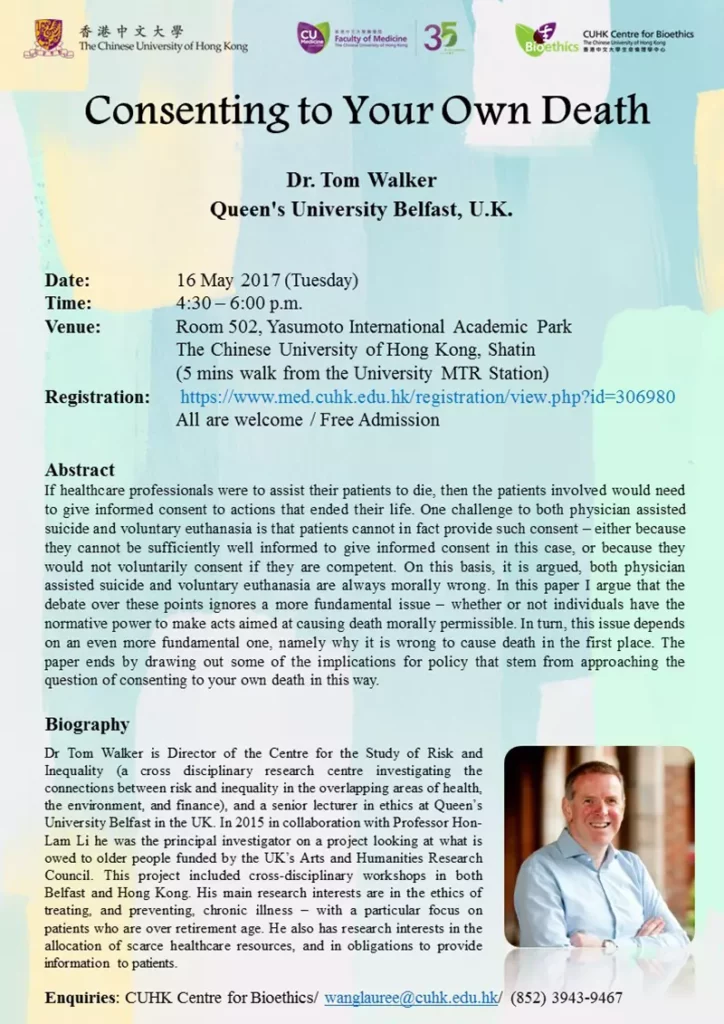
Date: 16 May 2017 (Tuesday) Time: 4:30 – 6:00 p.m. Venue: Room 502, Yasumo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Location Map: Please click here Speaker: Dr. Tom Walker Registration: Please click here Flyer: Please click here Event Recaps: Presentation slide by Dr. Tom Walker – “Consenting to Your Own Death”
1970年一個「生」字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5.5.2017)

1970年一個「生」字 我告訴朋友,現在做「生命倫理」(bioethics) 方面的工作,就有人問,什麼是生命倫理?試過幾種方式長話短說,都不能很滿意。 方才發覺,bioethics在香港還是一個生字,不只是冷僻,真像新名詞。 新加坡政府銳意發展生物科技及前沿研究,十多年前已知道需要預先建立生命倫理指引和法律框架。當年有份參與制定框架的學者專家包括Prof. Terry Kaan,現在是港大Centre for Medical Ethics and Law (CMEL) 的Co-Director。 在臺灣,「生命倫理」是高中生命教育概論課程的內容部分。我從網上讀到復興高中陳淑婉老師一篇題為「探討生命倫理與科技倫理的基本議題」的課程綱要,共四節課,並非蜻蜓點水。 Bioethics這個名詞,起於1970年美國。到80年代,「生命倫理學」已漸漸形成學術規模。但它不是傳統的獨立學科,因為生命倫理議題不是單一的學科可以完整地處理的。 生命倫理議題也不是純學術性的,很需要在公共空間作開放式討論。為此要多謝《信報》編輯部爽快地應允開闢這個每月一次的專題空間。 欄名定為《生命倫理線》,是從手掌掌紋「生命線」想起的。每一篇有關生命倫理議題的文章是一點,日積月累串起來便像一條「生命倫理線」。倘若社會上還有其他人穿針引線,就會結成網絡。 生命倫理網絡有什麼用?在臺灣社會,這成為生命教育的文化底子;在新加坡,生命倫理研究令相關的政策更成熟,更有認受性。 但也不是非得要功利地證明生命倫理有用的。在公民社會公共空間開闊一些視野,令多元觀點對話,本身便是件好事。 克羅地亞學者Ivan Segota屬於「生命倫理學」的第二代人,在90年代,他好奇地想,bioethics這個從70年代出現的字是誰發明的呢?像中國武俠小說裡尋找「宗師」(現實裡也有王家衛導演認真訪尋「一代宗師」) 那樣,他鍥而不捨地尋根,最後認定威斯康辛大學Madison分校的Prof. Van Rensselaer Potter (1911-2001)是bioethics的創始人。 Prof. Potter 當初自創這個由bio- 與ethics合成的新名詞,是為了表達一個理念:人類面對生物科技和生物醫學的爆炸性發展,需要有一座「橋」,跨專業學科,連接現在和未來;最終要讓科學實踐和價值觀共鑄未來,讓人類文化與大自然生命共存,才是真正的人類繁榮 (human flourishing) 。 最初他想過用bridge bioethics作為新理念的稱謂,最終簡稱為bioethics。他深信,「生命倫理」這一座橋,不能靠傳統醫德、專業觀念、科學或哲學各自為政來支撐。 我猜想,應該是60年代的生物醫學和科技在某方面的發展,令Potter預感到,人類在走進新世界。我溫習了一下: 1959 人工體外受精技術 1960 發明心肺復蘇術 (CPR) 1960 FDA批准使用口服避孕藥 1967 第一宗人類心臟移植 Potter是生物化學家,腫瘤學教授,在McArdle Laboratory for Cancer Research工作。他一定也看見生命科學(life sciences) 的突破。1962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頒給1953年在劍橋大學共同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Watson and Crick兩位科學家。Potter在一次國際生物倫理會議中以錄像演講,憶述自己是早在60年代初已開始思考生命科學與人類未來的宏觀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