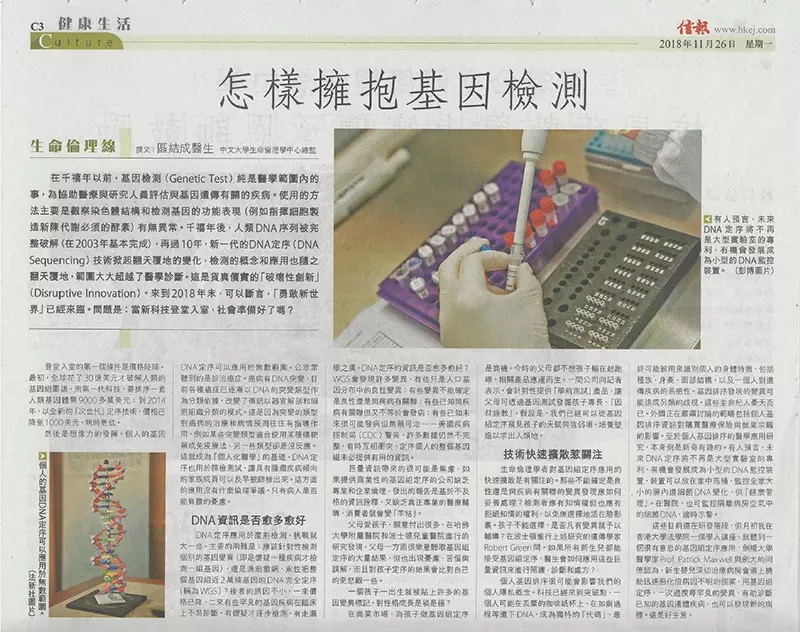怎样拥抱基因检测
在千禧年以前,基因检测(Genetic Test) 纯是医学范围内的事,为协助医疗与研究人员评估与基因遗传有关的疾病。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观察染色体结构和检测基因的菜单现(例如指挥细胞制造新陈代谢必需的酵素)有无异常。千禧年后,人类DNA序列被完整破解(在2003年基本完成) ,再过十年,新一代的DNA定序(DNA Sequencing) 技术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检测的概念和应用也随之翻天覆地,范围大大超越了医学诊断。这是货真价实的「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来到2018年末,可以断言,「勇敢新世界」已经来临。问题是:当新科技登堂入室,社会准备好了吗?
登堂入室的第一个条件是价格陡降。最初,全球花了30亿美元才破解人类的基因组图谱。用第一代科技,要排序一套人类基因体需9千多万美元;到2014年,以全新的「次世代」定序技术,价格已降至1000美元,现时更低。
然后是想象力的发挥。个人的基因DNA定序可以应用于无数范围。公众常听到的是诊治癌症。癌病有DNA突变,目前各种癌症已逐渐以DNA的突变类型作为分类依据,改变了传统以器官解剖和细胞组织分类的模式。这是因为突变的类型对癌病的治疗和病情预测往住有指导作用,例如某些突变类型适合使用某种标靶药或免疫疗法,另一些类型却是没反应。这就成为「个人化医学」的基础。DNA定序也用于筛检测试,让具有肿瘤疾病倾向的家族成员可以及早被筛检出来。这方面的应用没有什么伦理争议,只有病人是否能负担的忧虑。
DNA信息越多越好?
DNA定序应用于产前检测,挑战就大一些。主要的两难是:应该针对性检测个别的基因变异 (即是怀疑一种疾病才检测一组基因) ,还是渔翁撒网,索性把整个基因组近二万条基因的DNA完全定序(称为WGS)?后者的诱因不小,一来价格已降,二来有些罕见的基因疾病在临床上不易诊断,有怀疑才逐步检测,有走漏眼之虞。
DNA定序的信息是否越多越好?WGS会发现许多变异,有些只是人口基因分布中的良性的变异;有些变异不能确定是良性还是与疾病有关联;有些已知与疾病有关联但又不等于会发病;有些已知未来很可能发病但无药可治…。美国疾病控制局(CDC)警告,许多数据仍然不完整,有时互相冲突,定序个人的整个基因组未必提供有用的信息。
巨量信息带来的很可能是焦虑,如果提供商业性的基因组定序的公司缺乏专业和企业伦理,发出的报告是基于不及格的信息诠释,又缺乏真正专业的医疗辅导,消费者就会变「羊牯」。 父母爱孩子,愿意付出很多,在哈佛大学附属医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进行的研究发现,父母一方面很乐意听取基因组定序的大量结果,但也出现忧虑、苦恼与误解,而且对孩子定序的结果会比对自己的更悲观一些。
一个孩子一出生就被贴上许多的基因变异标记,对性格成长是祸是福?
在商业市场,为孩子做基因组定序是商机。今时的父母都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相关产品应运而生。一间公司向记者表示,会针对性提供「学前测试」产品,让父母可透过基因测试发掘孩子专长、「因材施教」。假设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基因组定序窥见孩子的天赋与强弱项,培养塑造以求出人头地。
技术快速扩散惹关注
生命伦理学者对基因组定序应用的快速扩散是有关注的。那些不能确定是良性还是与疾病有关联的变异发现应如何妥善处理?检测者应有知情权但也应有拒绝知情的权利,以免无选择地活在阴影里。孩子不能选择,是否凡有变异就予以辅导?在波士顿进行上述研究的遗传学家Robert Green问,如果所有新生儿都能接受基因组定序,医生会如何应用这些巨量信息来进行照护、诊断和处方?
个人基因排序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个人隐私概念。科技已经来到突破点,一个人可能在丢弃的咖啡纸杯上、在如厕过程等遗下DNA,成为独特的「代码」,最终可能被用来识别个人的身体特征、包括种族、身高、面部结构、以及一个人对遗传疾病的易感性。基因排序发现的变异可能做成另类的歧视,这些并非杞人忧天而已。外国正在严肃讨论的范畴包括个人基因排序信息对购买医疗保险与就业求职的影响。
至于个人基因排序的医学应用研究,本身倒是新奇有趣的。有人预言,未来DNA定序将不再是大型实验室的专利,有机会发展成为小型的DNA监控装置,装置可以放在家中马桶,监控全家大小的肠内道细菌DNA变化,供「健康管理」。在医院,也可监控隔离病房空气中的细菌DNA,适时示警。
这些目前还在研发阶段,但月初我在香港大学法学院一个学人讲座,就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基因组定序应用:剑桥大学医学家Prof. Patrick Maxwell与剑大的同僚认为,新生婴儿深切治疗病房会遇上机能迅速恶化但病因不明的个案,用基因组定序,一次过搜寻罕见的变异,有助诊断已知的基因遗体疾病,也可以发现新的病种。这是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