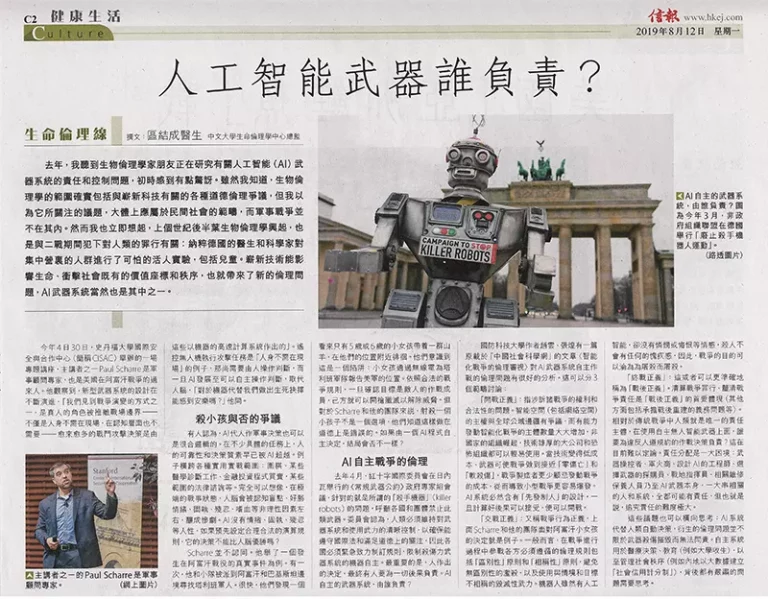報章專欄
2018年11月,時任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的賀建奎宣佈全球首宗經基因編輯的雙胞胎女嬰誕生,這項「世界第一」惹來國內外交相指責,他被拘留調查,不聞消息,直至上周初內地報道他被一審宣判干犯非法行醫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那對基因編輯嬰兒「露露」和「娜娜」的情況沒有公佈。基因編輯嬰兒是否一個「瘋狂科學家」的犯罪故事而已?本欄在2019年1月的一篇文章提出,「賀建奎事件」留給2019年兩份有迫切性的功課:給中國的功課是如何建立或改進對科學研究和人體科技試驗的管治;給科學界的功課是:能否釐清基因組編輯(genome...
這篇文章是在紐西蘭南島南端的城市鄧尼丁寫的,寫時理工大學的圍困還未解。早一星期我離港時,圍困爭持激烈,街上聚眾聲援,警方以催淚彈驅散,連伊利沙伯醫院也受到波及。抵達鄧尼丁,為我辦理入住旅館手續的是一位衣著整齊、談吐斯文的先生,禮貌地問我來參加什麼會議,我說關於法律和倫理。他又問我從哪裡來,聽到「香港」二字,就敏捷地反應道:「那你一定有很多法律和倫理問題可談了!」其實我來是談香港最近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的公眾諮詢。這位接待的先生似乎很清楚香港的困境,輕輕說:「雙方堅持不退讓,就沒法解決了。」我後來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律師。
這篇文章刊出時,慘烈的鬥爭已經持續了整整半年,期間許多既有的價值規範嚴重破損。有人哀嘆香港回不去了,甚至說,this...
香港劫難未過,社會撕裂之外,公眾對政府的基本信任也在快速蒸發。近例是食物及衞生局長在電視訪問中解說,催淚彈對身體造成不適僅是短暫,水炮車的顏色水劑亦是無毒,大多數市民人若非完全不信,也會覺得這是對公共健康風險的輕描淡寫。此時期,食衞局一些重要的政策事項仍在推進,祈盼社會公眾有成熟的就事論事的底子去看待。事項一是9月初食物及衛生局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向公眾諮詢;事項二是年初成立的基因組醫學督指導委員會近期完成了階段性工作,將就發展路向提出建議。我在兩個事項都有些機會直接或間接地提供一些意見。本文針對後者基因組醫學範圍的生物樣本庫(biobank,簡稱生物庫)...
青少年能有多自主?
青少年在作出關於自己的重要決定時,能有多大的自主權?對上一次我較為仔細地看這個問題是在兩年多前,當時香港社會在辯論應否放寬法例規定,以容許一名不滿18歲的少女捐贈活體器官給不幸急性肝衰竭的母親。當日社會的主流情緒傾向於同情,認為應該酌情容許例外。那還不止是一種情緒,人們是判斷少女心智成熟有如成人。數字上的年齡是死的,青少年的心智成熟可能因人而異。兩年之後的今天,香港處於凶猛的政治對抗之中,好像給送到另一個宇宙時空。今天來問同一問題:「青少年能有多自主?」情境完全不同了。
香港有保護兒童包括少年的傳統。保護兒童的法例反映了這一點,例如針對青少性行為有最低的合法年齡的規定,與16歲以下的兒童性交是刑事罪行,不可以解釋說這個15歲的少年特別成熟,有能力自主同意。
香港沒有統一的法定年齡。同意性行為的最低年齡為16歲,成人身份證在18歲時發放,但未經父母同意的合法結婚年齡為21歲。
法定年齡不一
法定年齡不一未必是不合理。青少年的自主能力不宜抽空地看,要考慮所作的決定有多複雜和有多大影響。年輕人年滿18歲就可以投票,但21歲或以上才能競選議會席位。邏輯很可能就是,議政是關係重大的,有較高的年齡要求不算不合理。當然也還可以爭論,為何訂在21歲?
有些法定年齡的差異不大合乎邏輯。例如青少年16歲可以同意性行為,但購買香煙和酒精的年齡為18歲。難道買香煙比性行為更嚴重?
更矛盾的年齡界線還有:法例容許年滿15歲從事全職工作,年滿13歲就可以兼職工作,但是少年卻不准「獨留在家」,否則父母可能被控疏忽照顧。邏輯在哪裡?難道在家比出外工作更危險?抑或是少年根本不適宜獨處?
在醫療方面,對青少年的自主也有規定,層次較多,但最少在邏輯上有一致性。一般來說,香以18歲分界,但不是絕對界線。醫務委員會《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守則》)這樣規定:「十八歲以下兒童給予的同意屬無效,除非該名兒童能明白所建議治療的性質和影響。如該名兒童未能明白所建議治療的性質和影響,必須取得兒童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同意。」(第2.12.1條)...
機構有病,員工吹哨?
在臺北一個生命倫理座談上,我們從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案例談到研究人員的失德行為,以及倫理教育的重要性。然後,我們討論為什麼單是倫理教育並不足以規範專業道德。一位來自愛丁堡的講者深思熟慮,輕聲提出一個問題:在你們的醫療體系中,最困擾醫生和護士的道德兩難處境(ethical...
人工智能武器誰負責?
去年,我聽到生物倫理學家朋友正在研究有關人工智能(AI)武器系統的責任和控制問題,初時感到有點驚訝。雖然我知道,生物倫理學的範圍確實包括與嶄新科技有關的各種道德倫理爭議,但我以為它所關注的議題,大體上應屬於民間社會的範疇,而軍事戰爭並不在其內。然而我也立即想起,上個世紀後半葉生物倫理學興起,也是與二戰期間犯下的對人類的罪行有關:納粹德國的醫生和科學家對集中營裡的人群進行了可怕的活人實驗,包括兒童。嶄新技術能影響生命、衝擊社會既有的價值座標和秩序,也就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AI武器系統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4日30日,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
醫護專業與病人私隱
六月充滿動蕩和衝突,在緊張複雜的警民與醫療互動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醫護人員有專業責任為病人保密,保護病人的福利,但是否同時需要與警方合作,甚至在某些情況底下違反為病人保密的原則?...
文化差異對(生命)倫理學有多重要?
四月時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了一場亞太區生命倫理教育研討會議,我們生命倫理學中心的副總監、中大哲學系教授李翰林在會議演講一個有意思的題目,聽者有共鳴。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似乎會對各種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問題便是一例。如果兩個文化在一個問題上互相分歧,兩個意見可以都是對的嗎?如果認為可以,那麼回答這問題的人就是來自「道德相對主義」(moral...
免責聲明
訪談和文章中所有觀點或意見均屬個人性質,並不代表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的立場或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