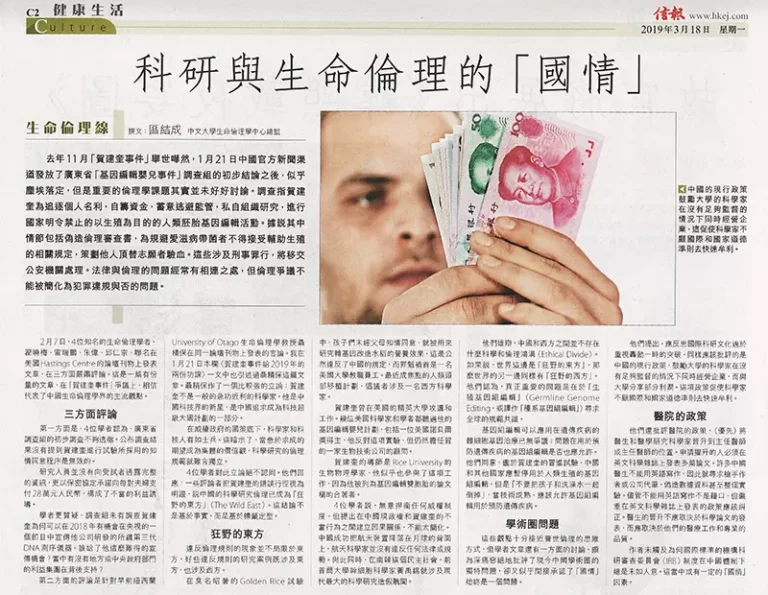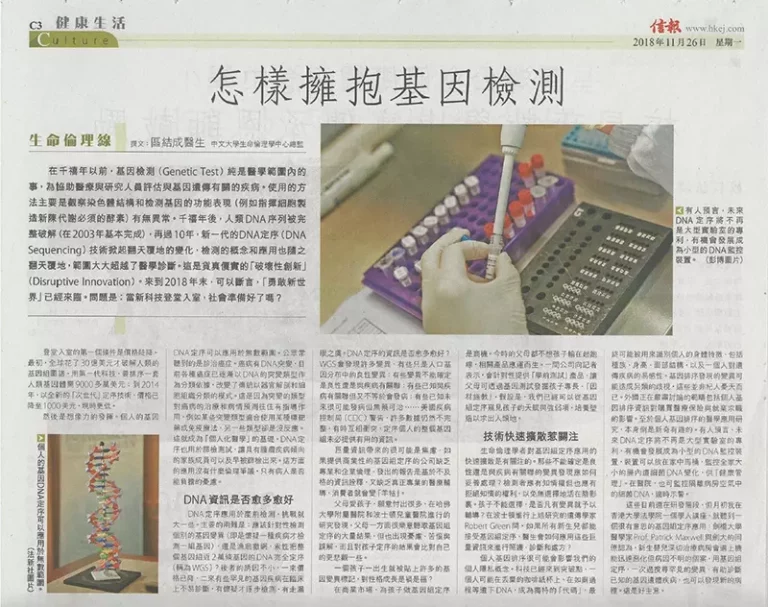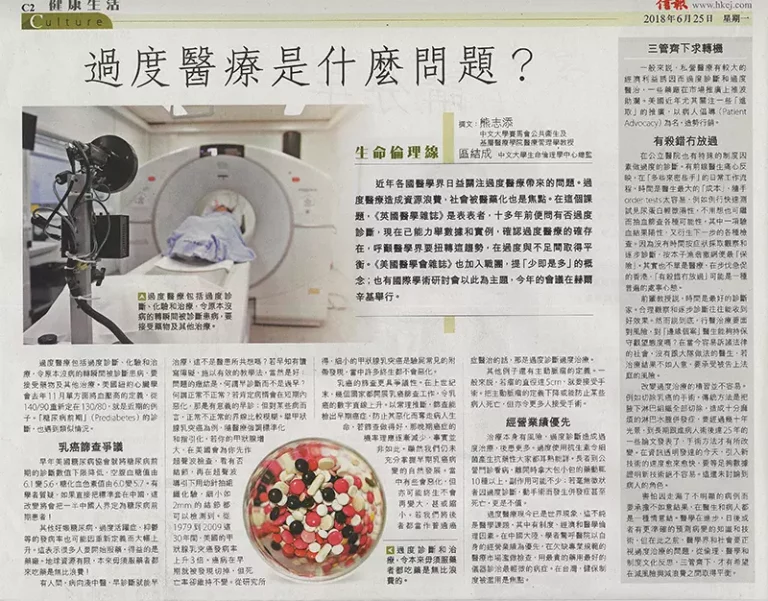报章专栏
科研与生命伦理的「国情」
去年11月「贺建奎事件」引发举世哗然,在1月21日中国官方新闻渠道发放了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的初步结论之后,似乎尘埃落定,但是重要的伦理学课题其实并未好好讨论。调查指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研究,进行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据说其中情节包括伪造伦理审查书、为规避艾滋病带菌者不得接受辅助生殖的相关规定,策画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这些涉及刑事罪行,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法律与伦理的问题经常有相连之处,但伦理争议不能被简化为犯罪违规与否的问题。
2月7日,四位知名的生命伦理学者,翟晓梅、雷瑞鹏、朱伟、邱仁宗,联名在美国Hastings...
我看公共医疗危机
农历新年前,前线医生和护士站出来,抗议公立医院病房在冬季流感潮底下的可怕状况。媒体纷纷说,公立医院病房「爆煲」了。在公众议论最热烈时,我婉拒了出席一个公开论坛的邀请。邀请者苏先生是我欣赏的一个节目主持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节目,拒绝时便感到有些歉意。我解释说,对于这个课题,我的想法不能在情绪最炽热的时候好好表达。而且,我两年前才从医管局的管理岗位退役,现在无论是在论坛讲解管理的挑战还是批评现况,都不大合适。
还有一个理由是,论坛的形式需要在舌剑唇枪中用三言两语就讲得清楚和表态。我不介意舌剑唇枪甚至擦出一些火花,但这两年间自己对医疗困局的思考,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渐渐用上了伦理学的角度。伦理学的角度不易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在高速对话中,伦理学的角度更容易被指「离地」。
在我的下一代当中有前线医生和护士,他们尽心工作打得捱得,但也很认同医生和护士工会是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我们常有交谈,因此我可以相当肯定自己在思考的事情并不「离地」,但这也一定不是「大路」的想法。
依我观察,类似的不满在去年和前年也有出现,媒体用「公立医院爆煲」起标题也有好几年了。今次与以前有两点不同:第一是表达愤怒的强烈程度和得到的广泛关注都是前所未见;第二是今次前线医护人员,无论在接受访问或是自发写文章,都能鲜明而细微地描绘出医院内恶劣的工作环境,令不满的情绪变得立体地有血有肉。
出现各执一端
我也注意到,一些舆论领袖和资深的私家医生加入了议论,评论文章掷地有声,而为危机把脉献策的人也不少。这却出现「各执一端」的现象,也就是说,各个论者依其洞见,声称已经为危机作出了无可置疑的「确诊」,但他们的诊断却各自不同:有人断定主因是医管局管理不善(或疏于改进)...
「贺建奎事件」给2019年的两份功课
权威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发布2018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榜,贺建奎位列榜单之中,但是以「反面人物」入选。他进行的「基因编辑婴儿试验」震动世界,「世界第一」并没有带来美誉。《自然》的特写文章说,「他在世界舞台上登场得匆匆,消失得也匆匆。...
问什么?
– 关于众人批评的编辑基因试验
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月底在香港举行,内容丰富但是焦点忽然落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副教授的冒进人体试验。他声称,全球首宗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双胞胎女婴露露及娜娜已诞生,其中一个婴儿「成功」剪掉CCR5基因,期望会增强对爱滋病的免疫力。...
怎样拥抱基因检测
在千禧年以前,基因检测(Genetic Test) 纯是医学范围内的事,为协助医疗与研究人员评估与基因遗传有关的疾病。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观察染色体结构和检测基因的菜单现(例如指挥细胞制造新陈代谢必需的酵素)有无异常。千禧年后,人类DNA序列被完整破解(在2003年基本完成)...
资助昂贵医药的伦理想法
昂贵医药令病人难以负担,是政治问题也是医疗伦理问题。香港的医疗政策,向来有这一道原则:「不应有人因缺乏金钱而不能获得适当医疗。」这道原则甚至写入《医院管理局条例》。就医管局的职能,第18条列明医管局可就公众使用医院服务须付的费用,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作出建议,建议须顾及以上原则。这基本上是一道伦理原则。问题有两个:一是何谓适当?二是医疗资源有限,而日新月异的医疗非常昂贵,真的人人可以获得吗?面对非常昂贵的治疗,有限的资源应当如何分配?
一旦这样提出问题,马上要接受两个前提。
第一,没有一个病人或一类病人可以期望无上限的医药资助。因为资源分配要考虑机会成本。
第二,资源分配必须公平而合理。读者会注意到,「不应有人因缺乏金钱而不能获得适当医疗」这一道原则,基本上就是从公平原则出发。香港是一个经济和商业主导的社会,但在医疗,这原则重视公平而非功利。
医疗「配给」是难题
关于医疗资源分配,有论者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配给」(Rationing)的难题。经历过二次大战和战后贫困的人,都深刻知道「配给」是怎样的。每人分到一些食物,没有人可以完全饱腹;每家分到一些煤炭燃油,没有家庭足够取暖过冬。这个概念用于医疗资源分配还是十分困难。每个病人平均分一点医疗,结果可能是「平等地」失救。外科医生不可以做十分一个手术,深切治疗病床不能每人轮流用一天。
考虑治疗效益是不可避免的。资源有限,高效益的治疗似乎应该优先。
医疗也有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治疗的效益是可以量化的。基本概念是成本效益分析(CEA)。
人皆有死,而无论预防或治疗,原则上应可减少死亡、延长寿命,或减少残障增益功能,或减少痛苦提升生命质量。这些可以用定量工具作换算。最常用的指标是QALY(Quality-adjusted...
道德异乡里的生命伦理
最近写书,来到一处谈Prof. H. T. Engelhardt 所讲的「道德异乡人」(moral strangers) ,上网查他的出生年,才知道他刚于今年6月逝世,享年77岁。他是医生、医学史家、哲学家、生命伦理学家。有段时期他数次来港访问,城市大学陶黎宝华教授和范瑞平教授是接待的主人家,后者曾是他的学生。我的职业生涯在医务而不在哲学,直接认识的生命伦理学家不多,几次见面畅谈,觉得很投契。
他声若洪钟,演讲恣意汪洋而逻辑严谨。他从不屑用PowerPoint。我笑问,你也难免用email吧?他也笑答,常记不住自己的电邮地址,还是爱书信往来。又加一句,用纸张不只是为沟通,像手抚着一本书,那种质感本身就是美学的经验!说时一脸陶醉的样子。
九十年代他首先发明moral...
一河之隔:病人知情权的差距
「政治正确」令如今行文上要避免「中港两地」的写法,以免误把香港划在中国之外,但在讨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病人知情权的时候,难免会讲「两地差距」 。过去四分一世纪,内地逐步改进有关病者知情权的规章和法例,两地差距正在缩窄,但一河之隔仍有差别,香港的病人知情权以个人权利为起点,内地较多以家庭为本,遇上严重或紧急情况,近亲主导医疗决定颇为常见,有时因非理性的决定引起悲剧,引发社会议论。在癌症病例,尤其多见向病者隐瞒病情。
改进起点
改进的起点,有人从1994年开始说,也有人从2002年说起。前者是针对医疗机构管理的行政法规,列明病者知情权包括了对自己的病情、诊断和治疗知情;后者针对的是进行的医疗活动时,应当由病者本人签署同意书。着手的方式是试行病历书写的基本规范,除了病者不具备行为能力之外,凡特殊检查、治疗、手术等,都要病人签署。
这在香港看来十分基本,但当年在内地是很大的一步了。支持和理解的医师认为,手术由病人自己签字,是尊重知情权也是尊重人权,但新规定给医生提出了新的课题,要让病人明白手术的风险又要让病人安心手术,并不简单。过去习惯向病人隐瞒病情,如今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也需要一个过程。有些医生,尤其是中医,就怀疑新的规定有没有好处,遗憾这忽视了签字对病者心理的影响。
更严重的异议说,从法律上讲,要病人签字很公平,但同意书把手术中、手术后可能出现的严重情况一一胪列,好像要病人签「生死契」,质疑是不是太残酷?是否缺少了人文关怀?
无论如何,改革没有止步。...
如何走下去 — 伦理与医疗
医学伦理的传统,在西医常上溯至「希氏誓章」( Hippocratic Oath ),来到现代则更新扩充为各式专业伦理守则。 传统上,专业伦理的关注在三个范畴:医患关系中的操守、与同侪的专业及利益关系,以及业务推广的规范。...
过度医疗是什么问题?
近年各国医学界日益关注过度医疗带来的问题。 过度医疗造成资源浪费,社会被医药化也是焦点。 在这个课题,英国医学杂志是表表者,十多年前便问有否过度诊断,现在已能力举数据和实例,确认过度医疗的确存在,呼吁医学界要扭转这趋势,在过度与不足间取得平衡。...
免责声明
访谈和文章中所有观点或意见均属个人性质,并不代表香港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的立场或意见。